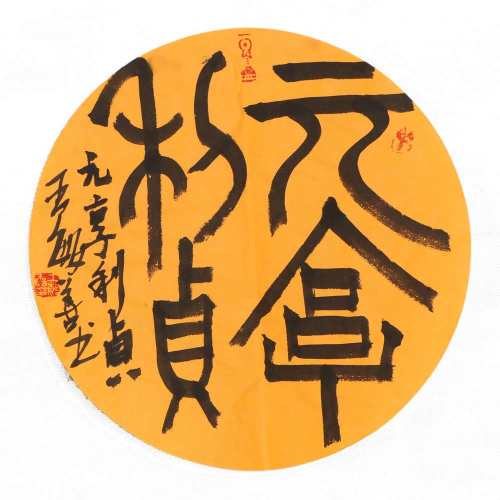风流在眼:晋王珣《伯远帖》的千年回响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浩如烟海的珍宝中,有一卷仅五行四十七字的墨迹,它静静地陈列,却承载着整个东晋时代的风流与气韵。这便是王珣的《伯远帖》。它不仅是一封信札,更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连接我们与那个“江左风流”之士人精神世界最直接、最可信的桥梁。

一、 希世之珍:晋人墨韵的唯一证言
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书法,尤其是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二王”书风,被誉为最高典范。然而,一个令人扼腕的现实是,王羲之并无一件确凿无疑的真迹传世,我们所见的《兰亭序》皆为摹本,《快雪时晴帖》亦是后人临摹或勾填。王献之的《中秋帖》也被考证为宋代米芾的临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伯远帖》的存在,便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史诗性意义。
它是“三希堂”中唯一的晋人真迹,非摹非临,纸墨苍古,笔触清晰,每一处飞白与顿挫,都是王珣当年手腕运动的真实记录。当我们凝视这片笔墨,便仿佛穿越了1600多年的时光,与那位琅琊名士面对面,亲眼见证他如何濡墨挥毫,将瞬间的情思凝固于方寸之间。这种“真”的价值,使其成为研究东晋书法笔法、墨法、章法最权威的“标准器”。
二、 笔墨形神:晋人风度的视觉呈现
《伯远帖》在艺术上完美诠释了“晋人尚韵”的美学追求。
其用笔,潇洒自然,以侧锋取势,灵动多姿。起笔往往顺势落纸,尖锋直入,流露出信手拈来的随意与自信。行笔过程中,提按转折极其丰富,如“從”字的最后一笔,由重至轻,飘逸而出;“優”字的笔画牵丝引带,婉转流畅。这些笔触毫无后世唐楷那般刻意求工的雕琢感,而是充满了即兴的、抒情的节奏,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是“自由潇洒的笔姿……摆脱了隶书的规律”。
其结字,疏朗开阔,奇正相生。通篇章法,错落有致,气脉贯通。字与字之间虽少连笔,但顾盼生姿,意断笔连。从“珣顿首顿首”的庄重开始,到“分别如昨,永为畴古”的感慨,情绪在笔端自然流淌,节奏也随之起伏。这种章法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书写者心绪轨迹的自然外化,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至高境界。
三、 文本与心境:书信背后的生命感怀
《伯远帖》的内容是一封写给族兄弟王穆(字伯远)的信。文中提到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己却“羸患”(身体羸弱多病),虽有“志在优游”的向往,却感叹“意不克申”(志向不能实现)。最后写道“分别如昨,永为畴古”,流露出对时光飞逝、友人远隔的深深怅惘。
这短短的文字,勾勒出一位东晋名士的典型心境:对友情的珍视,对自身健康的忧虑,对自由优游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世事无常面前的淡淡哀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私人化的情感絮语,而这恰恰是最真实、最动人的地方。王珣所代表的琅琊王氏,虽为顶级门阀,身处权力中心,但其个体的生命体验,依然充满了普通人的烦恼与感伤。这封短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褪去“书圣”家族光环的、有血有肉的文人形象。
四、 流传与升华:从私人信札到文化符号
《伯远帖》在历史上的流传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书画收藏史。它历经宋、明、清诸代宫廷与名家递藏,卷上留有董其昌、乾隆等人的题跋与鉴藏印。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其珍爱有加,将其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一同供养于养心殿的“三希堂”,使其地位升华至无以复加。
结语
《伯远帖》是一页薄纸,却重若千钧。它以其无可争议的真实性,让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原貌;以其精湛绝伦的艺术性,为我们树立了“尚韵”书风的典范;以其真挚动人的文本,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鲜活的情感脉搏。它不仅仅是一件书法作品,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一曲流淌的乐章,一个伟大时代精神气质的永恒回响。在它那疏朗的笔画间,东晋名士的从容、优雅与淡淡忧伤,依然在向我们低语,诉说着千年不变的风流。
撰文:王敏善,当代书家、一级美术师、知名撰稿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