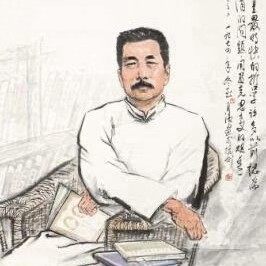栗晓读《白鲸》——我们都是佩科德号上的水手

啊,这头罕见的老鲸,置身于狂风暴雨,
海洋就是它的家,在这里强权就是公理,
而它便是一个强大的巨人,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称王称豪。
——《鲸鱼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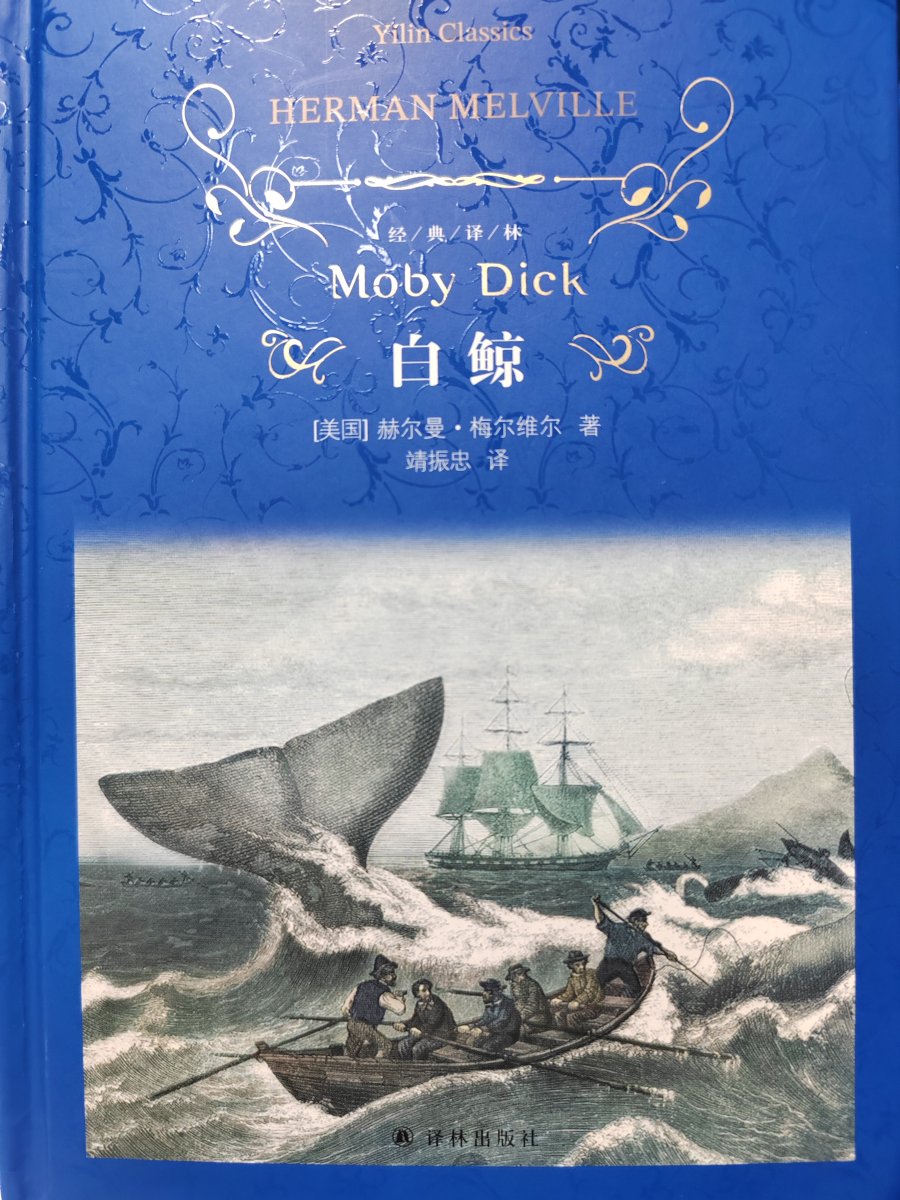
2025年春夏交替时节,看到《白鲸》这部著作,还是从格非《文明的边界》中阅读到的。滋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有《白鲸》作品的存在,更别说阅读了。
“叫我以实玛利吧。”《白鲸》在开头这样写道。在读完《白鲸》之后,更加觉得这个开头非常棒。它如此自然而顺滑地把读者拉进书里的世界。翻阅资料得知,原来《白鲸》的开头这句话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
《白鲸》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非常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但是,梅尔维尔生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有名人物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他的《白鲸》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其文学史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梅尔维尔一生充满传奇,他小时候家里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谋生,去船上当水手。他曾在南太平洋小岛与食人族之称的太平人共同生活过,在多艘船上当过捕鲸水手,甚至加入过海军。海洋是他第二故乡,这为他创造白鲸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北京》以捕鲸船——佩科德号追逐白鲸莫比·迪克为主线,通过船长亚哈的复仇执念与船员群体的命运交织,构建起融合航海历险、哲学思辨与生态警示的多元化叙事结构框架。
作品采用史诗笔法描绘海上生死博弈,兼具戏剧张力与象征深度。白鲸,象征自然力量,亚哈的执念映射人类对命运的抗争,最终船毁人亡的结局,揭示人与自然对立的悲剧性内核。
《白鲸》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和无尽的贪婪,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和报复。
阅读《白鲸》,你会随着佩科德号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那种天海一色的追逐鲸鱼的生活,充满着无限的压抑和惆怅,大海的尽头仍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而《白鲸》这首歌词,也是唯一的一首诗歌,才会让人轻松一些:
啊!大风快活无比,
鲸鱼喜欢逗乐儿,
还把尾巴挥舞,——
大海啊,你真是个风趣、活泼、好斗、俏皮、滑稽、爱愚弄人的家伙!
浪花四处飞溅,
那只是它在拌酒,
拌得泡沫四溢,——
大海啊,你真是个风趣、活泼、好斗、俏皮、滑稽、爱愚弄人的家伙!
雷霆劈裂船只,
那只是它在咂嘴,
品尝它的美酒,——
大海啊,你真是个风趣、活泼、好斗、俏皮、滑稽、爱愚弄人的家伙!
格非在《文明的边界》中写到,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袭,从而与自然达成一种平衡。但不幸的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绝不会止步于仅仅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反,它因其自身的目的和旅程,会持续不断地创造并繁殖新的欲望和需求从而来打破这种平衡。
换句话说,文化曾经保护并帮助过我们,而现在它终于变成了某种异化的力量。不光是伊格尔顿,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奥地利作家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也有类似的忧虑。比如说,志贺直哉就认为,人类一旦踏过自然与文明的平衡点。实际上已经上了一条不归路,从而必然会导致地球上“最后的人”的出现。
在《白鲸》中,叙事者曾多次对读者直接喊话:永远不要轻易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你一旦离开,实际上就回不去了。
而《白鲸》中的佩科德号正是这样一艘“不归之舟”。如果我们将佩科德号视为文明秩序的象征,那么,这艘船实际上已经越过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临界点或平衡点。
“我们都是佩科德号上的水手。”格菲在《文明的边界》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