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云飞/文
《学记》有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寥寥数语,勾勒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在这段话中,“道而弗牵”指向师生关系的和谐建构,“强而弗抑”关乎学习过程的动力机制,“开而弗达”则涉及思维训练的深度开启。三者共同指向“和易以思”这一教育理想境界,不仅是对教学方法的精妙总结,更是对教育伦理本质的深刻揭示。在当代教育面临技术理性过度扩张、人的异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学记》中这一教育智慧犹如穿越时空的光芒,为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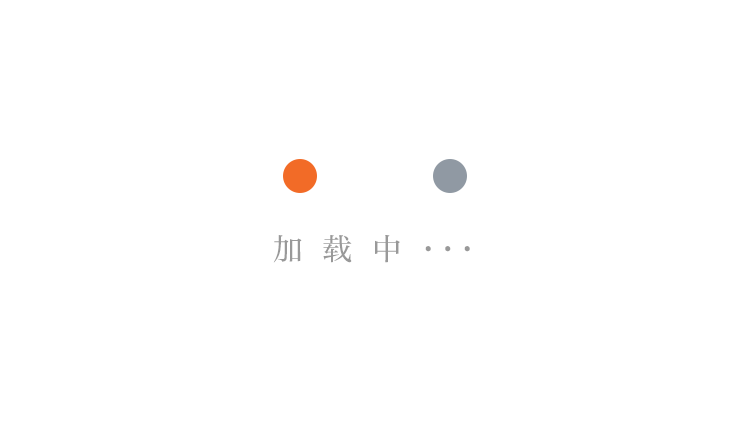
一、道而弗牵:教育作为相遇的伦理实践
“道而弗牵”四字,蕴含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师生关系的深刻理解。“道”即引导,如孔子所言“循循然善诱人”,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尊重的引领;“弗牵”则反对机械的强制与灌输,警惕教育中的暴力倾向。这一原则确立了教育作为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遇的伦理本质,在现代教育语境中愈发彰显其价值。
从哲学视角看,“道而弗牵”体现了教育的关系性本质。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区分了“我-它”和“我-你”两种关系模式:前者将他人视为可利用的客体,后者则是主体间的真诚相遇。“弗牵”正是避免将学生降格为被操纵的“它”,而“道”则是建立“我-你”式教育关系的积极实践。这种关系不追求控制而追求理解,不追求塑造而追求对话。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对话不是要使自己的观点获胜,而是要让自己冒险。”教育中的引导,正是这样一种师生共同“冒险”的过程——教师不是将学生引向已知的终点,而是与学生一同探索未知的可能。
中国传统书院制度堪称“道而弗牵”的典范。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不仅制定学规明确求学方向,更强调“问答之间,须是亲切”,注重师生间的质疑问难。明代东林书院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展现的正是这种开放而非强制、引导而非束缚的教育氛围。古代教育家强调“教学相长”,认为教育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双向的滋养,这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对话教学”、“协商课程”等理念不谋而合。
反观现代教育,技术理性往往将教育关系简化为知识传输的效率问题。量化考核、标准化测试、程式化教学,使教育越来越倾向于“牵”而非“道”。学生被当作需要填充的容器,而非有待点燃的火炬。这种教育模式导致的学习异化,不仅削弱了学习的内在动力,更损害了教育的伦理本质。正如弗莱雷所批判的:“教育变成了存款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存款人。”
“道而弗牵”启示我们,教育首先是一种伦理实践,其次才是知识传递。它要求教师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守望者而非塑造者,如同苏格拉底自称的“精神的助产士”。在信息爆炸的当代,这种教育观更具现实意义——教育的价值不再体现为信息传递的多寡,而体现在能否培养学生判断、选择与创造的能力。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而是成为学生探索世界的向导,与学生共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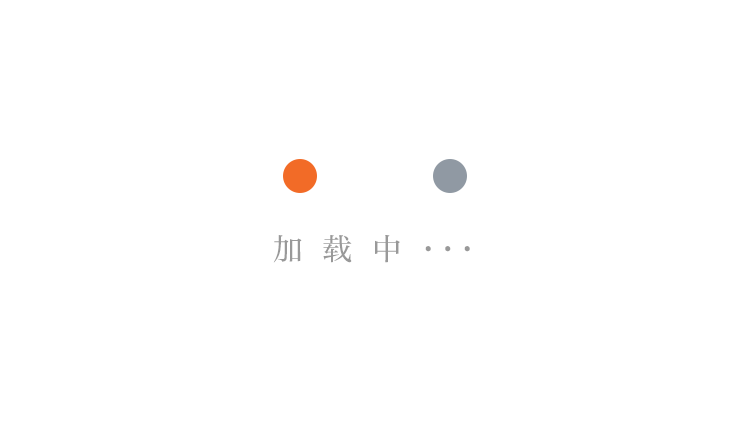
二、强而弗抑:教育激励的辩证智慧
“强而弗抑”揭示了教育过程中动力激发的艺术。“强”即鼓励、勉励,如《学记》前文所言“教人不能强而为之”,此处之“强”应作“激发”解;“弗抑”则反对压制、逼迫,避免挫伤学习热情。这一原则展现了教育激励的辩证智慧,在现代学习科学和动机理论中得到惊人印证。
从心理学视角看,“强而弗抑”契合了内在动机的保护与激发。德西和瑞安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人类有天生的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和关系性。真正的激励源于这些需求的满足,而非外部压力。“强”正是对学生自主探索的鼓励,对能力发展的支持;“弗抑”则是对控制性环境的警惕,避免损害学生的自主感。研究表明,外在奖励往往会削弱内在动机——当学习变为获取奖赏或避免惩罚的手段时,学习本身就异化了。
中国古代教育实践充满了“强而弗抑”的智慧。孔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感叹,并非道德谴责,而是对弟子向善的呼唤;他赞赏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体现的是对自发进取的肯定。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相信人人皆有自善自能的种子,教育只需“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使内在潜能自然发展。传统蒙学教育强调“循循善诱”,注重通过诗歌吟诵、故事讲述等方式激发童趣,而非机械灌输,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现代教育却常常陷入“抑”多于“强”的困境。过度竞争、分数至上、标准化评价,创造了压抑而非激励的学习环境。学生为外部指标而学,而非因内在兴趣而学。这种“抑”的教育导致创造力枯竭、学习焦虑加剧,甚至引发心理健康危机。正如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强调天赋的“固定型思维”会让学生害怕挑战,而关注过程的“成长型思维”才能激发持久动力。
“强而弗抑”启示我们,教育应建立激励而非压制的生态。这要求重新思考评价方式——减少横向比较,增加纵向成长评估;弱化高风险测试,强化形成性反馈;降低外部奖励,提升内在成就感。芬兰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印证了这一点:减少标准化考试,增加个性化指导,反而提升了整体教育质量。真正的“强”是赋能而非施压,是培养学生“学而不厌”的内在动力,使其成为终身学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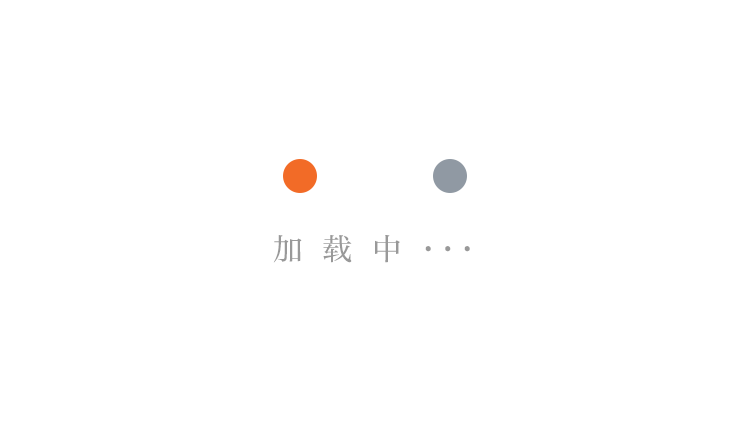
三、开而弗达:思维训练的深度与边界
“开而弗达”是教学艺术的高度凝练——“开”即启发、开启,如孔子所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弗达”则不直接给予答案,不越俎代庖。这一原则关乎思维训练的深度与边界,在现代教育注重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的背景下尤显珍贵。
从认知科学视角看,“开而弗达”符合思维发展的规律。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理想的教学应走在发展前面,但只能适度超前。“开”正是在学生认知边界上提供支架,引导他们跨越当前水平;“弗达”则避免提供完整答案,保留必要的认知挑战。研究表明,适度的认知冲突能促进深度思考,而过早提供答案则会终止思维过程。鲁文·弗因斯坦的“认知可塑性”研究也证明,通过 mediated learning experience(中介学习经验),教师可以“开”发学生的认知潜能,而不必“达”成具体结论。
中国传统教育中,“开而弗达”是最高教学境界。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充满启发而非灌输:“子曰:‘绘事后素。’子夏问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对话中,孔子用比喻“开”之,子夏举一反三,孔子进而赞赏这种思维跃迁。《学记》强调“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博喻”即多种方式的启发,而非单一答案的给予。朱熹读书法提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强调的不是知识的接收而是思维的主动建构。
现代教育却常常“达”而不“开”。标准化课程追求唯一正确答案,应试训练强调解题套路,许多教师急于“告知”而非“启发”。结果学生知识量增加,思维能力却停滞不前。OECD的PISA测试发现,许多学生能解答标准问题,却缺乏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种“达”的教育培养了“知道分子”而非“思考者”,与信息时代对创新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驰。
“开而弗达”启示我们,教育应重思维过程轻知识结论。这要求教师成为“问题制造者”而非“答案提供者”,设计开放性问题而非封闭性练习;创设认知冲突而非避免困惑;鼓励多元探索而非统一思路。正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所言:“科学是不确定的教导。”真正的教育不是传递确定性,而是培养在不确定性中思考的能力。在当下,知识获取变得便捷,教育的价值更加体现在培养学生提出新问题、思考新可能的能力上,“开而弗达”的原则因此更具当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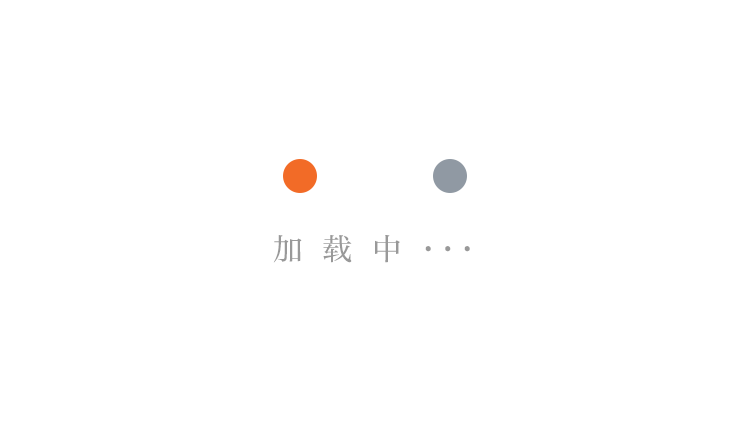
四、和易以思:教育理想的当代重构
“和易以思”是“善喻”教育的整体效果:“和”指师生关系的和谐,“易”指学习过程的愉悦,“思”指思维活动的深度。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教育的理想境界。在当代教育语境中,这一古典理想需要被重新诠释与重构。
从教育哲学看,“和易以思”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关注手段效率,价值理性关注目的意义。现代教育危机实质是工具理性过度扩张,价值理性日益萎缩。“和易以思”则恢复了教育的价值维度:“和”关乎教育的人际维度,重建师生作为人的相遇;“易”关乎教育的情感维度,恢复学习的内在乐趣;“思”关乎教育的智识维度,重申思维培养的核心地位。这三者共同对抗教育的异化,回归教育的本真价值。
在传统教育智慧与现代教育科学的对话中,“和易以思”获得新的生命力。神经教育学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易”)促进学习效率,安全环境(“和”)利于大脑开放,挑战性任务(“思”)激发神经可塑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社会互动(“和”)、内在动机(“易”)和认知冲突(“思”)的学习价值。这些科学研究与古典智慧惊人地一致,证明《学记》的教育原则具有跨时代的有效性。
面对当代教育挑战,“和易以思”提供了改革方向。在宏观层面,教育政策应从单纯追求效率转向关注整体教育体验,减少控制性指标,增加支持性环境。在中观层面,学校应创建学习共同体而非竞争场域,强调合作而非排名,注重成长而非成绩。在微观层面,教师应实践对话式教学,设计启发式问题,建立信任型师生关系。
特别在数字时代,“和易以思”原则至关重要。技术不应加剧教育的非人化,而应增强人的连接(“和”);不应使学习变得枯燥,而应增加(“易”);不应替代思考,而应促进更高阶思维(“思”)。教育科技的真正价值不是让教育更“高效”,而是让“和易以思”更充分地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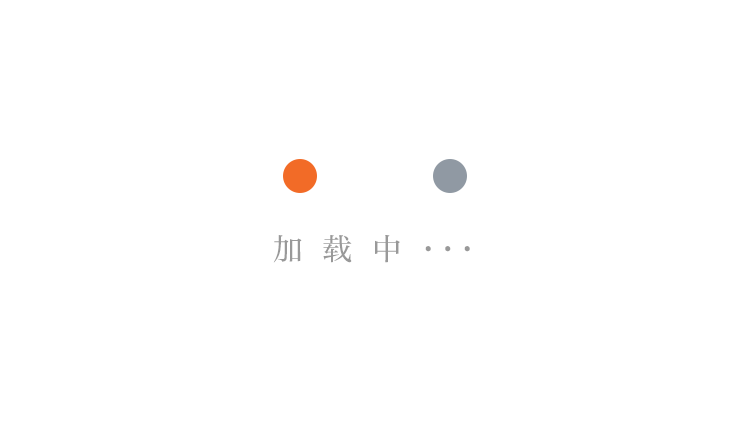
结语:走向和易以思的教育未来
《学记》云:“君子之教喻也”,一个“喻”字道尽教育真谛——不是灌输而是启发,不是塑造而是引导,不是控制而是唤醒。“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不是具体教学方法,而是教育的基本伦理态度;“和易以思”不是量化指标,而是教育的应然状态。
在人类文明面临深刻转折的今天,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其本质。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成长,而非知识和认识的堆集。”《学记》的教育智慧提醒我们,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对话;不仅是技能的培训,更是思维的开启;不仅是社会的需要,更是人的自我实现。
走向未来,教育应超越功利主义桎梏,重建“和”的师生关系;超越异化学习,恢复“易”的学习体验;超越表层认知,达成“思”的深度训练。这需要教育者拥有古典的智慧与现代的视野,需要教育系统平衡传统与创新、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
“和易以思”不仅是古代教育的理想,也是未来教育的指南。在这个意义上,《学记》不再是一部古老文献,而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宣言——它呼唤一种尊重人的主体性、激发内在动力、培养批判思维的教育,一种真正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的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完成其最崇高的使命:不仅培养有能力的人,更培育有思想、有情怀、有自由意志的完整的人。
作者:
孟云飞,出生于河南,199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1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师从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兼任河南大学文学院书法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博士生导师。
其作品多次参加各种比赛、展览并获奖。书法风格潇洒豪放、妍美质朴,尤其注重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在“书法风格”研究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0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新华文摘》《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书法》等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出版《二王书艺研究》等专著,主编《翰墨情缘》《艺海无涯》以及《中小学书法教材》等四十余本;录制《轻松学书法》系列光盘十余张,并在“中国教育”等多家电视台播出;主持、参加《书法风格研究》等省部级以及国家艺术科学规划等项目;曾获得文学艺术评论、国家第四十三批博士后基金等奖项。
本文为正观号作者或机构在正观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正观新闻的观点和立场,正观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