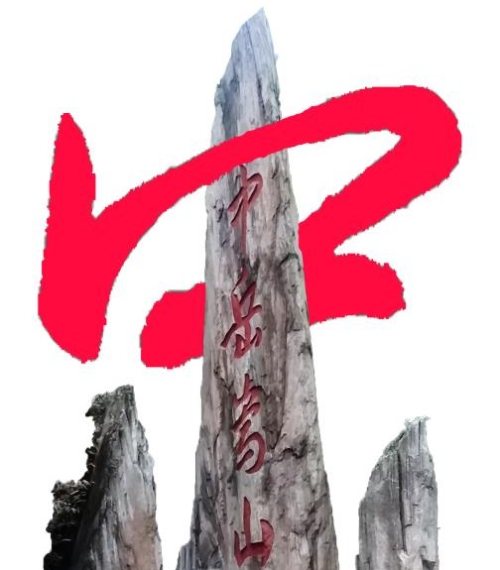我的老师倪春正


作者:刘曙光
今晨又读《论语》篇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句,仿佛今天之我与孔老夫子的学生曾点之“志”也有趋近了。这几句话是老夫子问及学生之志时,曾点之答,不知曾点当时有多大年岁。
名师出高徒。人非生而知之,何人不从师?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是在并列之尊的序列的,可见“师”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俗言曰“师徒如父子”。重教首先是尊师,不尊重老师,是谈不上重视教育的。

我出生于上世纪“文革”开始之年。我们村在嵩山脚下,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不到200口人。因为偏僻,因为贫穷,村里的孩子谁也没有上过幼儿园,七岁入学是那时的规定。我们的村子小,只有两个教室,一个教室坐的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另一个教室坐的是四、五年级的学生。我们把这种班叫“复式班”。全校只有一个“公立”老师,另一个老师是我们村配的“民办”老师。一年级写生字,二年级作算术题,三年级的孩子则挪移到教室的前排听老师讲课,经常是如此循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教我们的公立老师姓倪,叫倪春正。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老师,除了教课,还教我们唱歌,教体育,也教我们学凫水,他最大的特点是爱逗孩子们玩,他和我们“玩”起来,也绝然是童心不泯,童态可掬。我和他常玩一种叫“跳茅缸”或“憋死牛”的游戏。即在地上画一个三条边的正方形,在没有画的一条边的中间画个O(当作茅缸),再画两条对角线,在相对的两条边的两端我们各摆两颗小石头子或土坷垃,两人的石子或土坷垃是不同的,然后一先一后,顺着对角线的四个端点和对角线的交叉点移动石头子,若谁的两颗石头子和O在一条线上就算输了。做这种游戏,不知怎的,他总老输我。输了的他,会拳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我头上轻敲两下,然后笑着说“你真是个小膈应蛋”。
他讲课很有趣味,时常逗我们乐。有一次,他讲《半夜鸡叫》那篇课文,他在讲台上捏了鼻子,扯开嗓子学起了公鸡叫,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他却平静如水。之后,我们暗地里都叫他“老公鸡老师”。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的年龄还没有今天的我大呢。他爱逗乐,我也偏爱和他逗乐。
三年级的后半期,我学会了推桶箍(即推铁环),他以为推桶箍会影响我学习,不准我把桶箍带进教室。一天下午放学后,我用墨水在我挨着的教室墙壁上画了个桶箍的图形,第二天早读时,被他发现了,他让全班同学停止了早读,愤愤地走到我的座位前伸手去墙上抓,结果是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也笑得停不下来。最后送给我的仍旧是两个“脑瓜崩”和一句话一一“你真是个小膈应蛋”。
我内心知道他是很喜欢我的,因为每次考试我就没落过前两名,再者是轮到我们家管他吃饭时,总是鸡蛋、豆腐、白油馍,白面条让他吃舒服。那时鸡蛋比较希缺,我奶奶和母亲经常是把两个鸡蛋和着半碗黄黍黍面糊一起煎。这年春天,我的大妹出生,家里攒了三四十个鸡蛋准备让我母亲吃,我爷爷说“把先生侍候好了,咱孩子才会学成事,长学问,有出息”。那个月我家把母亲坐月子才吃的鸡蛋也分给了倪老师吃,对此,我母亲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她还生怕老师吃不好。我们家当时是大人口,爷爷、父母、两个叔叔、两个婶婶、一个姑姑都是壮劳力,挣工分的人多,所以不太缺吃的,全家人最期盼的是老师能看重我,把我培养成才,因为我是“长子长孙”的身份。
倪老师一个月大约在我家吃四五天饭。当年老师在谁家吃饭,那是谁家的荣耀。老师轮到谁家吃饭,这家的当家人要到学校去请,并且还要陪吃饭。轮到我家请老师吃饭,总是我爷爷去请,爷爷作陪。我企盼老师到我家吃饭,也是有我的小秘密的。我们家当时有一条“家规”是老师吃完饭,由我把碗端回灶屋,大人们是想借此机会加深我和老师的感情。不知他是怎么知道我家的这条“家规”的,反正每次我去收碗筷时,他总要给我留几片煎鸡蛋,几块炒豆腐或是一牙白油馍,然后默不作声地看着我吞咽下去。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管公立老师吃饭,老师一天要给管饭之家一斤粮票、三毛三分钱。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初夏,小满过后,又下了几场雨,村西的小河开始涨水了,有几个清澈的水潭可以洗澡凫水了。我还不会凫水,但倪老师可是个凫水高手,村上人说往年他们见过倪老师一个猛子扎下去能在水下呆两三分钟,有一次人们还见他抓了一条老鲇鱼上来。
那几天不知怎的,他在我家连着吃了几天饭,于是我就缠着他给我学凫水。油菜割罢,麦子还没有熟,还不到放麦假的时候,我学会了凫水。那年的暮春初夏,我跟着倪老师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到村西的小池潭里凫水寻乐。印象最深的是某天下午,凫水寻乐后,他穿着一件白背心褂子,衬衣搭在肩膀上,一路啍着歌曲而归;我呢?只穿了个小裤头,光着脚丫子跟在他身后,我的手上还提了一串用细柳树枝串着的十几条小鱼,那种快乐,那种恬淡而又洒脱的幸福感,永生不忘。那些鱼是倪老师的劳动成果,也是我俩那天晚饭的牙祭。今早又读上述的《论语》那篇时,这一幕一下子又呈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清晰的如在眼前了。
该上四年级时,我到外公外婆家去上学了,他们村子大,有小学,还有初中。那几年,除了假期,我吃住基本上都在外公外婆家。之后,上高中,读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忙忙碌碌几十年,很少再见到过倪老师,只是偶儿也听到些他的音讯。如今,倪老师下世有二十多年了,当年的那个我也已五十六岁了。
重温两千五百多年前,孔老夫子与学生曾点浴乎沂后而言志之乐,使我想起了因管老师吃饭,我学会了凫水,想到了逮鱼,想到了快乐的童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中之志是何呢?我看“志在求得心乐也”;如若不乐,何以“咏而归”?乐又在何处呢?我看“乐在无念无虑也”。这两句是我胡猜的。原文真正要表达的“志”和“乐”,我似乎能感觉到,但又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