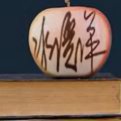雨打山阶夜渐凉

作者: 冰溪洋

山里头的雨,总爱挑着初秋的傍晚往下落。风裹着涧水的凉意在沟谷里打转,先撩得崖边刚绽瓣的野菊晃了晃,沾在嫩黄花瓣上的草屑被吹起,轻飘飘落进晒谷场的竹筛——筛子里摊着半干的板栗,是前两日上山捡的新果,雨丝斜斜打在褐红的壳上,沙沙响,像谁在轻轻翻拣去年收的旧棉絮。
七点光景,山村里的灯盏刚亮几盏,昏黄的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纸,在雨幕里晕出一小片暖。石阶上的青苔被雨浇得发亮,背着竹篓的妇人从坡下上来,裤脚卷到膝盖,沾着新泥点,手里攥着半袋刚从镇上买的感冒药——是给家里受了凉的婆婆买的,初秋的雨最易浸寒,药袋边角被雨泡软,里头的说明书露一角,字晕得看不清。
“慢些走哟!”坡上屋檐下有人喊,是守着小卖部的李大娘。她织针别在衣襟上,伸手要帮妇人拢紧竹篓绳,线团在脚边滚半圈,又拽回来,针脚还挂着半截灰毛线——那是给村西头五保户织的薄线衣,初秋夜凉,得赶在霜降前织好。“这雨要下到后半夜!明早山路滑得能摔屁股墩儿,实在要出门就拄根拐棍!我灶上温着姜茶,进来喝口驱驱寒再走嘛!”
妇人笑着摆摆手,脚步没停。竹篓里的青菜叶还滴着雨,顺着篓底缝隙往下淌,在石阶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她匆匆的身影。方才在镇上药房,医生反复说“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她早刻在心里,哪用看那晕字的说明书?山里头的女人,哪回不是踩着初秋的冷雨撑起日子?只是这回想着婆婆咳得发紧的声儿,脚步比往常更急了些。
村东头的老磨坊还亮着灯。磨盘转动声混在雨声里,闷闷的,像山在轻轻喘气。磨坊的门没关严,挂着的旧布帘被风吹得晃来晃去,能看见里头的柱子——三十来岁的汉子,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却仍弓着腰稳稳推磨,帮隔壁独居的张大爷磨新收的早稻。初秋的稻谷刚晒干,磨出的米带着新米的香。
张大爷的腿去年摔了,走不动路,柱子每次去镇上拉货,都会绕到他家,把晒得干爽的稻谷扛到磨坊。磨好的米他用布袋分几次送过去,有时还捎把自家菜园刚拔的青萝卜——初秋的萝卜脆生生,熬汤正合适。柱子的竹刮子把湿谷壳扫到墙角,留着晒干当柴。“再磨两筛就够您吃一阵子了!”他对着里屋喊,声音里带着点喘。
张大爷的咳嗽声从屋里传出来,带着点沙哑:“柱子啊,歇会儿喝口热水,看你额头上的汗。我灶上温着红薯,是窖里存的头茬儿,甜得很,你尝尝。”
柱子应着,手里的动作没停,磨杆压在肩上,磨盘转得更稳了。
雨越密,打在磨坊的木屋顶上,噼啪响,像有人在屋顶撒豆子。檐角的排水管早堵了,雨水顺着房檐往下淌,在地上冲出道小沟,沟里的水裹着泥,往坡下的公路流去。
沟边的蒲公英还没谢尽,被雨冲得东倒西歪,根却扎在土里,毛茸茸的花盘贴着地面——初秋的雨虽凉,却浇不透这韧劲,等雨一停,说不定又能冒新芽。山里头的草木都这样,经得住初秋的雨打,也耐得住夜凉。
坡下的公路上,一辆蓝色货车慢慢开过来,车灯把雨丝照得像金线,在黑夜里扯出长长的光带,车轮碾过积水路面,溅起半尺高的水花。驾驶室方向盘上贴着送货清单,王婶家的名字打了个勾,车斗里装着水泥,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边角用绳子扎紧——司机老王早检查了三遍,这水泥是王婶家盖新房用的,初秋雨水少,正赶工期,耽误不得。
他探出头,对着路边岔路口喊:“王婶在家不?你家盖新房的水泥送到喽!”
岔路口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王婶举着伞跑出来。伞是旧的,伞骨断了一根,用红绳子绑着——那绳子还是去年儿子结婚时剩的。身后跟着她男人,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束在雨里晃来晃去,照见院角晒着的茶籽,摊在竹席上,被雨打湿大半,正往下滴水。初秋的茶籽刚摘下来,得趁着晴天晒干,不然容易霉。
“可把你盼来了!”王婶的声音裹着雨丝,带着点急,“这雨下的,还以为你今晚不过来,生怕耽误明早砌墙。”
老王笑着跳下车,裤脚沾了一路泥,鞋底子还卡着小石子。他弯腰抠出来扔到路边:“说好了今晚送,哪能误工期?你们盖房是大事,我这货车跑山路虽慢,却不能掉链子!茶籽别急,等雨停了我帮你们搭棚子晒,车上有多余的塑料布,厚实得能挡秋寒!”
三个人合力把水泥袋搬下来,雨珠顺着帽檐往下滴,落在水泥袋上,很快洇出一小片深色。王婶要留老王喝热汤:“灶上温着红薯稀饭,就着腌萝卜干,香得很,你喝一碗驱驱寒再走。”
老王摆着手往驾驶室走:“不了不了,前头还有两家等着送,晚了山路更难走,跟踩棉花似的!等你们新房盖好,我再来喝喜酒,尝尝婶子腌的腊肉——去年初秋尝过一回,香得我到现在还惦记!”
车灯再次亮起时,车后窗已蒙了一层水汽。王婶站在路边挥手,直到那点光亮拐过山弯,融进雨夜里,才转身往屋里走。伞沿的雨水滴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混着男人手里手电筒的光,暖融融的,把院角的茶籽照得发亮。
雨还在下,山村里的灯盏渐渐多了,一盏挨着一盏,像散在黑夜里的星星。有谁家的收音机开着,声音不大,透过雨幕飘过来,能听见里头说今年茶籽收成好,镇上再过半月就来收,价格比去年高两成——初秋的收成,总让人心里踏实。
屋檐下的燕子窝被雨打湿了,泥巴黏在房梁上,几只小燕子缩在窝里,叽叽叫着。燕子妈妈从雨里飞回来,嘴里叼着虫子,翅膀上的羽毛湿得往下垂,却还是稳稳地落在窝边——初秋快到迁徙的时候了,得趁着天没太冷,多喂些虫子给雏鸟。它把虫子小心地喂进小燕子嘴里,自己抖了抖翅膀,又扎进雨里。
石阶上的水洼里,映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还映着檐下的灯晃悠悠。有风吹过,带来远处山涧清浅的流水声,混着村里的狗吠,还有谁家孩子的笑声——是隔壁的小虎,正趴在窗台上看雨,手里拿着妈妈刚给做的布老虎。布老虎的耳朵缝着补丁,是用小虎去年穿的薄棉袄改的,初秋穿不着厚衣,改个玩具正合适。他攥得紧紧的,嘴里还念叨着“明天雨停了要去捡板栗,还要帮奶奶剥刺壳,晒在院里等爸爸回来吃”。
这笑声在雨夜里轻轻荡开,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水里,漾开圈圈暖意。山里头的初秋夜,因这场雨显得格外静,可这静里,藏着的都是暖乎乎的事儿:是药袋里裹着的牵挂,是毛衣针上绕着的惦记,是磨盘里转着的帮衬,是车轮上载着的守信。
雨丝还在飘,夜渐渐深了,山阶上的凉意又重了几分。可山村里的每一盏灯,每一扇窗,都透着让人安心的暖。这暖像坡上刚栽的茶苗,经了初秋的雨,根才扎得更稳;像山涧里的水,绕着石头,也能稳稳地往前流。
等明天雨停了,太阳出来,山阶上的青苔会更绿,野菊花会开得更艳。那些扛着锄头、背着竹篓的身影,又会出现在山间的小路上——有的去坡地给茶苗松松土,有的去晒场上翻晒板栗,有的背着竹筐去摘最后一茬儿秋茶。檐下的灯还会亮着,照着晒场上的板栗,照着磨坊的石磨,也照着满是盼头的日子。
作者简介:冰溪洋(系笔名),原名杨锡冰,男,河南信阳商城人,娱评人、知名散文创作者、资深博主,河南省微电影协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其大量作品覆盖中国作家网、央视网、人民网、凤凰网、中国知网、大河网、顶端新闻、大象新闻、今日头条、百度新闻、网易新闻、搜狐新闻、简书等众多主流网络平台。曾荣获责任中国——人民网2011年度、2012年度十大社会责任博客,人民网2014年度十大微博网友;央视网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精英博主奖、2012年度十大人气草根博主奖、2013年度十大草根名博;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2024年度顶端文学十佳散文创作者、2024顶端人气创作者TOP100;入围“博客十年——影响中国百名博客评选”200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