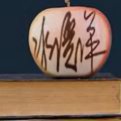冰溪洋‖一碗凉白开

作者:冰溪洋

日头正毒的时候,柏油路晒得泛着油光,风刮过来都是热的,裹着田地里的土腥味,扑在脸上像贴了片暖烘烘的粗布。
田埂上的人刚把最后一捆稻子扛上板车,麻绳勒得肩膀发疼。腰杆还没完全直起来,粗布褂子就顺着脊背淌汗——早浸透了,贴在身上像块湿抹布,一动就黏得慌。额前碎头发全黏在脑门上,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有的滴在板车木把手上,晕开一小圈湿痕又很快干了;有的砸在滚烫地上,“吱”一声就没了影,连点痕迹都留不下。
他张了张嘴想喘气,喉咙里干得发紧,像有团晒干的麦秸在里头烧,连鼻腔都冒着火气。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望,村口小卖部的招牌在晃眼阳光里糊成一团。可这会儿就算有冰镇汽水、裹着糖精的果汁摆跟前,也比不上一口凉水实在。
板车轱辘碾过村口石子路,“咯吱咯吱”响得跟老驴喘气似的,每颠一下,肩膀的酸痛就往骨头缝里钻。推开门进了堂屋,先往八仙桌上瞅——搪瓷壶果然搁在桌角阴凉里,壶身还带着点沁人的凉意,是早上烧的开水,晾了大半天,正好凉透了。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抓起桌边粗瓷大碗。碗沿还沾着昨天喝玉米糊糊的印子,也没顾上擦。掀开壶盖,凉水“哗啦啦”往碗里流,那声音脆生生的,比院角蝉鸣还让人熨帖。碗壁很快凝了层细密水珠,顺着碗边往下滴,落在桌布上晕开小水点。手指刚碰到碗沿,就打了个激灵——那股凉劲儿顺着指尖往胳膊上窜,连汗毛孔都好像缩了缩。
端起碗,嘴唇刚碰到冰凉碗沿,就迫不及待喝了一大口。凉水先润了润干裂的嘴唇,再顺着喉咙往下滑,像条清凉小溪淌过焦灼土地:喉咙里的烧灼感慢慢退了,一股凉意往肚子里沉,又顺着血管往四肢百骸钻。后背的汗好像都跟着凉了,黏在身上的褂子也不那么硌得慌,连太阳穴突突跳的燥热,都轻了下去。
“咕咚、咕咚”,两口下去,大半碗水见了底。他放下碗,长长舒了口气,胸口里的闷热气像是被这碗水浇灭了,连呼吸都变轻快。再咂咂嘴,嘴里竟漫开淡淡的甜——不是冰糖的腻甜,也不是糖水的齁甜,是渴到极致时,干净凉水裹着生活本味的甜,从舌尖一直漫到心里头,连牙根都清爽。
想起去年夏天在镇上卸水泥,三十来袋扛完,浑身的灰跟刚从土里爬出来似的,连睫毛上都沾着粉。老板递过来一瓶冰镇可乐,捏在手里冰得手疼,拧开盖子“滋啦”冒气。喝一口甜得发腻,咽下去胃里还泛酸,末了嘴里黏糊糊的,倒不如回家端起粗瓷碗喝凉白开痛快。
那时候村里老支书就坐在门槛上抽烟,瞅着他笑:“娃啊,饭要吃热的,水要喝凉的,日子要过踏实的——花里胡哨的东西,顶不上一口实在的。”
现在他也坐在自家门槛上,风从门洞里吹进来,带着院里头老槐树的阴凉,扫过胳膊上的汗,沁得人舒服。又倒了半碗凉白开,慢慢抿着,碗里的水映着头顶房梁,晃悠悠的。眼瞅着墙根下鸡窝旁,媳妇刚摘的黄瓜还沾着泥,绿莹莹的——晚上煮玉米糁子,就着腌黄瓜吃,再配半碗凉白开,清爽的滋味该和这水是一样的。
这日子是累,春耕时天不亮就下地,露水打湿裤脚;秋收时晒得掉皮,汗珠子摔八瓣。可累极了有口凉水解渴,饿极了有口热饭填肚子,就觉得心里满当当的。电视里常演城里人的日子,顿顿有鱼有肉,喝的饮料装在好看的瓶子里。可那些东西看着热闹,倒不如这碗凉白开——不掺假、不花哨,喝下去能熨帖到心里。现在的年轻人爱买甜水,说有滋味,可他们没尝过,在日头下熬过半日,一口凉白开的甜,才是能渗进骨头里的甜。
日头慢慢往西斜了,院子里的影子拉长了,老槐树的影子罩住了大半个门槛。他把空碗放进盆里,又拿起搪瓷壶,往壶里续了点新烧的开水——明天还要早起去割剩下的半亩稻子,早上晾上,中午回来又能喝到凉丝丝的白开。
晨光里会再晾起这只搪瓷壶,午后又会有粗瓷碗盛着清凉。一碗碗水,陪着他把日子过下去。
作者简介:冰溪洋(系笔名),原名杨锡冰,男,河南信阳商城人,娱评人、知名散文创作者、资深博主,河南省微电影协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其大量作品覆盖中国作家网、央视网、人民网、凤凰网、中国知网、大河网、顶端新闻、大象新闻、今日头条、百度新闻、网易新闻、搜狐新闻、简书等众多主流网络平台。曾荣获责任中国——人民网2011年度、2012年度十大社会责任博客,人民网2014年度十大微博网友;央视网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精英博主奖、2012年度十大人气草根博主奖、2013年度十大草根名博;河南日报社顶端新闻2024年度顶端文学十佳散文创作者、2024顶端人气创作者TOP100;入围“博客十年——影响中国百名博客评选”200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