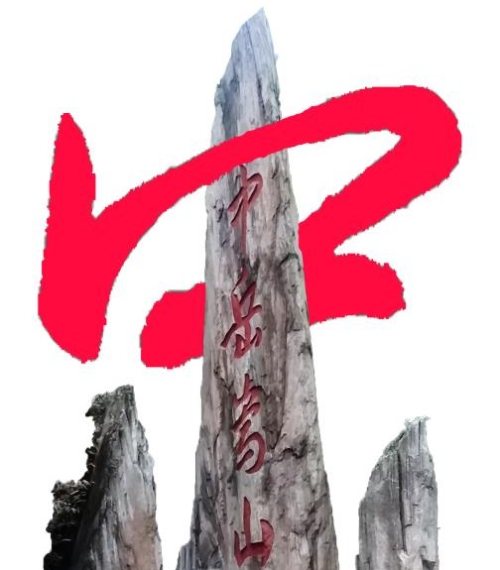山村小学琐记


少室山东麓、少林河畔有马庄、尚庄、张庄、王庄、祖家庄、刘庄、张店等一溜儿村庄,古代称为一溜儿石纽屯,张庄居中。村的中央有座古庙,初建于清咸丰年间,1952年改建成学校。1972年我开始在本村上小学。
俺家距学校不远,学校没有院墙,中间隔两户人家,20多步的距离。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上学非常方便。我说件小事,你听了就会心生羡慕的。一年级时,有次俺班下课稍晚一会儿,有个小伙伴急着撒尿,因茅厕太小,高年级学生早已站满,他挤不进去,又不敢在厕外小便,禁不住尿湿了裤子。而我则跑回家去,轻松得到了解决,既积了肥,又行了方便,一举两得。这种自豪感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小学时光。
那时学校的条件极为艰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课桌都是用泥坯盘的,凳子都是从家里搬的,黑板全是用黑漆抹的。课余活动也十分简单,天冷时就靠着墙挤挤暖和,天热时就在河边打打水漂。比较高雅的活动,便是男孩的“斗鸡”“打面包”和女孩的“跳房子”“踢踺子”,当然,最快活是“六月六发大水”时,在铺满石板的街道上打水仗。
老师的办公条件也是捉襟见肘,大队为了补贴学校,在少林河边为学校分了一片薄田,让师生勤工俭学。每到周六下午,学生们便有了用武之地。学校会安排三、四年级的学生去西坡拾羊屎蛋儿,五年级的学生往地里抬茅粪。抬茅粪可是个苦差事,闻着臭味忽略不说,大粪溅到身上暂且不提,一旦不小心打破了瓦制的粪桶,既不敢报告老师,也下敢让大人知道,那种窘迫和胆怯最终还是遮掩不了。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年学校种的萝卜很给面子,获得了丰收。收获的那天,晚霞也在少室山巅凑着热闹,久久不愿离去。
记得从二年级开始,我对春天有着特别的期待,刚刚入夏,就盼着下一个春天快快到来,因为在这个季节,可以听到燕子的呢喃,能够在液窝里暖出绒绒的蚕宝宝。到了小麦抽穗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山林里捉蝎子,卖蝎子的钱用以购买连环画。我最爱看小人书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三国演义》《鸡毛信》……,成了要好的朋友,陪我走过知识匮乏的少年时期。
那年月,农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农闲时能够看场电影对山里人是一种奢望。村落小,街道也就窄狭。放电影时连块像样的场地都不容易找到,学校前的十字路口就成了难得的选择。那天夜里,全村男女老少走出家门,将十字路口塞得非常瓷实。为了能看到全屏,我和一位小伙伴煞费苦心,才得以如愿以偿。
三年级的教室原是中王大殿,大殿后有个小风道管。我俩像小蜘蛛,撑着两边墙壁,手抬脚移,麻利地攀到一侧的平房上,然后顺着大殿的瓦房坡爬到房脊。为了避开别人的视线,我俩趴在房坡上不敢乱动,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早已没了“冷”的概念。直到散场时,才感觉冻木的双脚已不听使唤。
我上四年级时,父亲来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那时几位老师是轮流值班的,他们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也要打理办公室的卫生,还要做些添煤封火、敲钟之类的杂活。
一天早晨,兄弟感冒需要去卫生所看医生,我们踏着雪先去了学校。父亲打开办公室的门,将煤火收拾好后,让我一边烤着火,一边等着桌上的闹钟,以便到点时替他去敲起床钟。我看着“嘀嗒嘀嗒”的闹钟,总嫌走得太慢,距到点还有三分钟时,我迫不及待来到屋檐的钟下,站在椅子上拉起钟绳使劲摇起来。我打包票,那是在山村荡起的时间最长、声音最亮、传播最远的一次钟声。
我也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时刻。那天,我们在生产队的麦场里上了一节体育课,返回教室时,一位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而引起跛脚的同学,悄悄贴着我耳朵说:“毛主席不在了。”“你胡说,看我们让公安局的人来抓你!”大家义愤填膺,真想揍他一顿。可小喇叭里传来的哀乐声证明了他没有欺骗大家。没过几天,大队部里设立了灵堂,同学们胸带白花、排着队列,站在毛主席的遗像前鞠躬默哀。走出灵堂,哭声一片。那是我所经历的最为悲痛的日子!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从外地调来一位姓张的校长,他因稍瘦而显得身材高大,向后梳理的背头自带稳重的气质。除了管理学校事务外,他还担着我们的语文课。那时的早自习对学生来说是场灾难,因为“掏钱难买天明觉”,小学生瞌睡大老是睡不醒。好不容易打着哈欠走进教室,又不知道去学习,不是喷空儿,就是吵闹。每当张校长悄悄推门走进教室时,同学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拿起书本,装作读书的样子,抑仰顿挫地大声朗读起来。这种小伎俩怎能瞒过校长犀利的眼晴,张校长自有高招。他知道我调皮,就让我去当班长,并且找来一本作文选,让我在黑板上写,同学们在本子上抄。第二天早上背诵,谁会背了,放学可以回家吃早饭;不会背的,让家长来领人。这招可真毒,没过多长时间,就治住了全班几十位“小猴精”。
张校长时常教育我们“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我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发奋学习的。那时语文考卷满分是100分,基础知识占60分,作文占40分。作文一般有两个题目,学生们可自选一题。那次期中考试,我语文考了117分。同学们很惊异,都认为是老师搞错了,张校长将谜底告诉了大家:我写了两篇作文!又过了半个学期,我以全班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全村改革开放后进城工作比较早的农家孩子。
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有多少事情已被岁月抹去。能够勾起这些回忆,说明这些事情已根植心灵的的深处。前几年我回到老家看看老宅,路过山村的中央,学校早已夷为平地。当年三年级的几间教室,重修后恢复成中王大殿和观音大殿,旁边竖着两通重修碑。几位老者坐在前檐下聊着往事,他们的话题中不知道有没有我小时候的影子。我有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作者:郜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