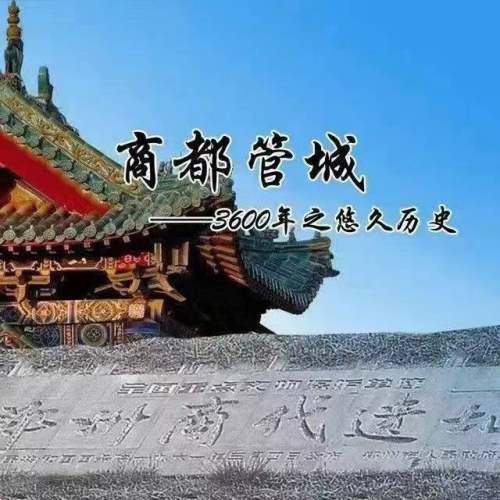照进乡村一束光——想起俺村郑州知青陈年往事

作者 胡全良
最近,又看到有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错误相提并论,斥为一场“错误运动”,为此颇为愤慨。那些遥远的记忆,那些鲜活的音容笑貌,瞬间奔涌而至。知识青年,这群来自远方大城市的“星光”,曾照进我的村庄,照亮我的童年。他们曾与我哥弟姐弟般相处。他们的成长故事,他们的亲历岁月,足以对那些道听途说、甚至蓄意制造的舆论迷雾,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六十年代末,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领着十来个背着背包、提着网兜的郑州城市青年,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豫东平原上的赵庄生产队。长期处于封闭环境、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男女社员和孩子们像看戏一样,观看、议论着这帮十七八岁的小青年。
生产队队部兼会议室腾出来了,土坯垒起的床铺上铺了席子,储备粮里匀出了麦子玉米,灶台配齐了崭新的锅碗瓢盆……“拎包入住”进来,生产队干部觉得知青们应该吃住无忧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不会套驴子磨面,不会生土灶做饭,村里干净利落的妇女队长手把手地教他们;不会干农活,不会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周全的老贫农代表像待自家孩子一般,教他们“做好自己”,学着耕耘土地,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打成一片。
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懵懂无知的时候。偷个鸡蛋解解馋,跟小学生拌嘴急了隔墙扔块儿砖头,甚至内部彼此间产生些小摩擦,类似事情都曾有过。但在贫下中农眼里,这不过是离巢雏鸟初试羽翼的稚嫩,不足与他们计较。宽容与引导,是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本性。渐渐地,生涩褪去,知青们学会了弯腰干活,学会了出力流汗,学会了为人处事。有人主动找叔叔大伯学种庄稼,有人抽空与婶子大娘家长里短,有人当起生产队文化教员,有人主动挑起技术性不强但比较苦累的担子……
有个叫杨义海的男知青,觉得自己干农活不在行,便自告奋勇帮生产队放养生猪,每天将各家各户散养的生猪集中起来牧养,以免其乱跑乱窗窜损坏集体庄稼。而与杨哥一起放猪时的交往交流,成了我童年时代一段最斑斓的记忆。
刚上一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跟着杨义海把猪群赶到野外空旷的池塘里洗澡、打泥、吃水草。泥泞塘埂上,杨义海说声“老弟,哥给你说”,便打开话匣子,讲大城市里柏油马路,讲公园里旋转木马,讲家里电灯下读书学习,讲城市男女青年交流交往,还故意逗我讲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从未出过三门四户的泥巴孩子,第一次知道外部世界的辽阔与精彩。原来世界是如此开阔广大,原来生活可以有不同模样,原来书本里藏着通向远方的路径。那些故事,像一粒粒种子在我贫瘠心田里生根。正是由杨哥亲手点燃的憧憬,成了我拼命读书、最终捧上“铁饭碗”的原始动力。可以说,没有知青哥哥姐姐带来的这扇“窗”,难有我今天进入城市生活、过上小康光景这扇“门”。
农村从不亏待实诚人。表现好、肯出力、谦虚踏实的知青,总能得到乡亲们有限但真诚的回馈。女知青张中宝就是如此。她不仅踏实肯干,还特会做人做事,见了年纪大的叫大爷大娘,见了年纪轻的叫大哥大姐,见了小孩叫弟弟妹妹,谁见了她、她见了谁都亲切自然。社员们先是推荐她当记工员,后来让她当生产队会计,队委会专门还向大队党支部推荐她入党。知道她家生活困难,生产队还给她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她探亲回家,婶子大娘们总不忘往她包里塞几个鸡蛋、装几把青菜。这份情谊,早已超越邻里界限,沉淀为城市青年与农民兄弟姐妹的深情。即便她们回城多年,也不忘给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写信联系,述说相互间情感,表达对社员们的谢意。
张新洲在当时知青队年龄最小,也是被公认最调皮捣蛋的,成天没个正型,常惹些祸端。两三年后,他变得既会处理关系,又能出力流汗,还成了种棉能手。回城后,他几乎挨家挨户给赵庄人写信表达谢意。后来有社员到郑州办事,他不仅热情接待,还协调关系帮助把事办妥。办事社员回村,夸他像变了个人似的。
张中宝回城后,家中依然经济困难,尤其是口粮不够吃,在写信交流时,谈到这一情况。社员们同情她,主动给她家寄粮食度难关。我家大哥多次想方设法弄些当时比较珍贵的全国流通粮票,给她寄过去救急。一根细细的邮线,牵系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
工分,是当时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有了工分,就能分到粮食有饭吃。村里记工分,男劳力十二分,女劳力十分。给这些刚出校门的知青,直接按最高标准记工分:男十二分、女十分。起初,只要他们人到场,不管待多久,都记满工分。后来,知青内部有异议,觉得干多干少不能一样。为此,生产队改成按出勤时间记工分,只要他们人到现场干活,都记半天分。这份“优待”,与其说是制度“漏洞”,不如说是社员对城里娃子一种朴素的体谅与包容。
知青点,是我每天上学路上最向往的“圣地”。他们刷牙用的牙膏、亮晶晶的牙刷、擦皮鞋的鞋油,还有涂脸的雪花膏……连同他们洋气的穿戴和举止,在没见过世面、破衣烂衫的孩子眼中,无异于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总想长长见识,扒着知青宿舍门框举目张望。开始,“丑小鸭”并不招他们待见。慢慢地,他们喜欢上了我,有的还与我成为“忘年”兄弟姐妹。
美丽动人的方惠君姐姐,长有一对俏皮的虎牙,满面笑容下藏着一副柔软热心。她见我亲切地叫“弟弟”,还让我喊她“小方姐姐”。每天清晨、中午“路过”知青点,她都会特意打开那宝贝似的收音机,让歌声伴我上学。她的善良,赢得全队男女老少的喜爱。然而,命运似乎对她有些苛刻。同伴们一个个回城了,因家庭成份不好、人也不够“灵活”等,她回城较晚。永远记得那天,她眼睛红红的,噙着泪对我说:“弟弟,姐姐今天心情不好,就不给你放歌听了……”那无助泪光,像根刺扎在我幼小心灵里。
不久,小方姐姐终于回城了。临行那天,我上学路过知青点。她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弟弟,姐姐有机会回来看你,你长大也要去郑州看姐姐哟!”自她回城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些知青哥哥姐姐们。出来工作这些年,常听说有当年知青回村“探亲”,一直没有机会遇上。
前些年,一股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将知识青年下乡描绘得暗无天日,充斥着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打骂侮辱”,甚至“霸凌强奸”。尤其那个嫁给美国人又被抛弃的演员陈冲。导演的那部博得西方青睐的《天浴》,更是将这种污名化推向极致。至今,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流毒影响还未清肃。对此,我唯有愤怒与痛心。当时接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地方毕竟较少,普通人不明就里,常被这些不怀好意的大V公知忽悠。我觉得,是时候不再让这种歪风邪气侵害国民思想了。
在记忆里,我们赵庄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多高素质、多大格局,但主流是宽厚、是善良、是互助。诚然,有方姐姐那样的委屈,有个别人初期的顽劣,有工分制度的磨合,但那绝不是时代的全部底色。我亲眼所见的是,乡亲们像对待自家孩子般接纳、教导,是知青磨砺中褪去青涩变得坚韧,是杨哥为我点燃梦想之火,是张姐与乡亲建立深厚情谊,是方姐纯净善良温柔。深信赵庄生产队的故事,也是全国千千万万个知青点的故事。这,才是那段真实、温暖的历史重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一次重大社会动员。对于知青个体,是广阔天地间摔打成长的大好时机,是城市青年与基层民众建立血肉联系的“开心一刻”,其中难免有不一样的酸甜苦辣。而对于偏僻乡村及其孩童来说,他们就是照进人民群众闭塞生活的“星光”。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劳力(尽管初期贡献有限),更是城市文明的微风,是外部世界的图景,是改变命运的启蒙。他们的故事,如一张张七彩碎片,拼接起农村农民精神世界的最初版图,照亮人们的未来岁月。这份由特殊年代孕育的城乡之间、知识青年与农民兄弟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联结,无论如何评说,都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剥离的温暖和力量。
当年青涩懵懂的年轻哥哥姐姐们,如今应该是七旬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了。几十年未见未知,你们生活得还好吗?我也早已离开赵庄,来到大城市生活。我知道,这片你们曾挥洒过青春汗水的土地,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尽管当初照顾你们、安慰你们、共同奋斗的大爷大妈、大哥大姐未必还在人世,但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永远记住你们带来的星光。如果情况允许,赵庄及豫东平原的父老乡亲永远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回家看看”。

胡全良,男,河南驻马店市人,军队退休干部,大校军衔,先后在团、师、集团军、军区宣传部门工作,曾有千万文字见诸媒体,有两部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