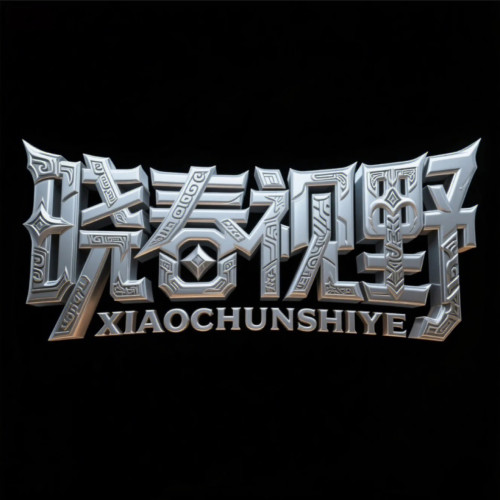砖上春秋见,字里乾坤藏:“雪泥鸿爪——浙东文字砖上的书迹流变”展观赏记

作者:杨 桦
9月2日,金秋初启。由文成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文成县博物馆承办的“雪泥鸿爪——浙东文字砖上的书迹流变”特展,在文成县博物馆一楼展厅隆重开幕。我久仰宁波古砖收藏大家程健捷先生,为了抢先一饱眼福,早上七点从温州驱车赶赴文成大峃。甫抵县文化广场,寻访着博物馆,在大门口不远处便遇到了从宁波来的文博、非遗、摄影与文化界一众人士,以及程先生本人。径入展厅,只见一方方承载千年时光的文字砖静卧于展柜,灯光下,砖面的包浆泛着温润光泽,与墙面题展名相呼应,瞬间营造出“与古为徒”的观展氛围,足见策展者对器物与空间关系的精准把控。
此次展览以“时间轴”为叙事主线,遴选汉、东吴、两晋、南朝、唐、宋六代浙东铭文砖及画像砖珍品,脉络清晰,断代明确,堪称浙东地区文字砖遗存的一次系统性梳理。细观展品,汉砖书迹最具“原生性”——笔画以刀刻为主,线条雄健开张,不拘一格,“蚕头燕尾”的雏形隐现却未循成规,尽显秦汉书法“鸿濛初开”的朴拙气象,如展陈的“永和九年”纪年砖,字形偏方,笔画间带着率性的“飞白”,是汉晋民间书风的典型遗存。
至东吴、两晋时期,砖文书风渐变。展品中一方东吴“天纪二年”砖,字形趋扁,笔画转折处多了几分圆融,已可见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痕迹;而东晋“咸康三年”砖则更为灵动,线条纤细却不失骨力,部分笔画出现“使转”,显露出士大夫书法审美对民间工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字砖,既是建筑构件,亦是社会文化的“微观载体”,砖上除纪年外,还见“吉语”“地名”等铭文,如“富贵祥宜侯王”砖,文字与砖面布局巧妙结合,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印证了当时“以砖记事”的社会风尚。
入唐及宋,砖文书风臻于成熟。唐代“天宝九载”砖书迹严谨规整,笔画粗细均匀,结体端庄,已完全褪去隶意,尽显楷书“法度森严”的时代特征;宋代“治平二年”砖则更添灵动,部分字迹带行书笔意,笔画连绵却不潦草,可见“尚意”书风对民间刻砖的渗透。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还展出数方图案砖,文字与纹样互为表里,字随形走,纹映字生,将“书画同源”的理念融入砖模艺术,足见当时工匠的艺术巧思。
从文物价值而言,浙东文字砖的特殊性尤为凸显。南方温润潮湿的气候,致使纸帛墨迹难存,碑刻摩崖亦存世稀少,而文字砖以陶土为质,经高温烧制后质地坚硬,得以跨越千年保存,恰好填补了汉晋至唐宋时期浙东地区书法演变的“实物空白”。此次展出的砖铭,既有官方纪年,亦有民间俗字,字体涵盖篆、隶、楷、行等,堪称一部“刻在砖上的中国书法演变史”,其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在南方地区同期文物中实属罕见。
观展至尾,再品“雪泥鸿爪”之题,愈觉精妙。苏轼“泥上偶然留指爪”的诗意,恰与文字砖的“偶然性”相契合——这些砖本为筑城、造墓之用,却因砖上铭文,成为文明的“意外见证者”。一方砖,便是一段微缩的历史;一笔划,便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印记。展柜中,砖面的裂痕、刻痕的深浅,皆是时光留下的“密码”,触摸砖面的粗糙质感,仿佛能与千年前的工匠对话,感受他们以刀为笔、以砖为纸时的专注与匠心。
离开展厅时,阳光正炽。回望展厅,那些沉默的文字砖依旧静立,却似在诉说着中华文脉的绵延不绝。此次《雪泥鸿爪》展,以小见大,以砖为媒,不仅让观众领略了浙东文字砖的独特魅力,更以专业的策展逻辑、清晰的叙事脉络,为区域性文物特展树立了典范。于文博研究者而言,它是浙东书法史与建筑史研究的“活素材”;于收藏爱好者而言,它提供了文字砖断代、辨伪的“实物参照”;于普通观众而言,它则打开了一扇触摸千年文明的“窗口”。砖上春秋短,字里乾坤长,这场展览,堪称一次兼具学术性与观赏性的文化盛宴。
( 作者:温州市收藏家协会顾问、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2025年9月2日匆草于寄吾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