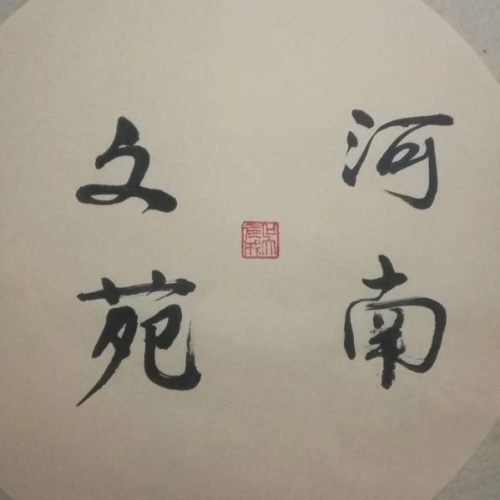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文留随想》(55)我必须固守着根植着的“境界”—为《中国诗人》而写诗随笔|匡文留专栏(137)

我必须固守着根植着的“境界”
——为《中国诗人》而写诗随笔

曾经有一度,我目光苍凉、头脑空洞、不知所云又无所适从,躯壳般机械地任由日月这无情的轨道抛来甩去,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并迅速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是1996年早春,我居住的这座西部高原古城雨雪交加、寒凛透骨,雨雪交加中卵翼庇护我几乎大半生的慈蔼父亲猝然离去,我在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瞬间之后,对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恍然大悟且痛彻肝肺。相当一度,我浑浑噩噩,提笔纸上便落满了对父亲的回忆和思念,除了连篇累牍地抒写和父亲有关的散文之外,我觉得自己连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恰恰也正是这前后,好多好多年来我必须源源不断汲取爱情的诗歌灵感与激情竟无奈地悄悄走向了死亡,我差不多以自杀式的理智和明察将这一次的“与爱壮别”称之为“最后一次失恋”。
这是很多年前自己的一小段文字,关于岁月,关于生命,更关于诗。我该深感庆幸的是,那段时日之后,我很快地振作起来,蓬勃起来,因为,是诗拯救了我。自此我便无比清晰地明白了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同“写诗”早已相熔相铸,无法背弃。
岁月是把杀猪刀。这真的是一句很民俗很民情的大实话,虽然过于赤裸,也显得市井了点儿,但没有谁会不感叹其直抵生命内核的力度与深刻的哲思。这样一把刀,年年岁岁一点一滴杀掉杀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令人不堪与惊悸的是同身体如影随形的“境界”。
说得明白一些,简单一些,这样一把刀,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将我们生命中曾经的美好和珍贵一样一样地杀掉、杀死了。任目光和心情溯流而上,自己的确丢失了太多太多的热爱与珍贵。那么,再细细地检点一下、审视一下,时至今日,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中,究竟还有什么形而上的“境界”,依然固守着、根植着,一如孩子的眼眸,仍不倦地追寻并欢欣于属于自己的一树葳蕤?
这无疑就是诗了。几十年倥偬而逝,时至今日,也唯有写着诗,自己才依然是自己,生命才依然活泼着美丽着,生活才依然生动着多彩着。
我之所以一直不停地写诗,是因为我太需要一个相濡以沫的爱人了,一个生生死死的情人,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真正的知己。
2019年1月20日

匡文留,当代著名诗人。满族,生于北京,长于大西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记者。现在北京兼职、写作。获“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首届唐刚诗歌奖终身荣誉奖。
1980年步入诗坛,在全国二百多家报刊发表诗作三千多首,作品被收入百余种选集并介绍到国外。出版诗集《爱的河》《女性的沙漠》《第二性迷宫》《西部女性》《情人泊》《女孩日记》《匡文留抒情诗》《爱狱》《灵魂在舞蹈》《另一种围城》《古都·诗魂》《我乘风归来》《回眸青春》《匡文留诗选》《大地之脐》,长诗《满族辞典》,散文诗集《走过寂寞》《少女四季》,散文集《姐妹散文》《诗人笔记》《围城内外》,诗论集《匡文留与诗》《匡文留诗世界》,长篇小说《花季不是梦》《体验》《我的爱在飞》,长篇纪实《少女隐情》《我爱北京》《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十部专集。多次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简介与创作收入国内外近百部权威性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