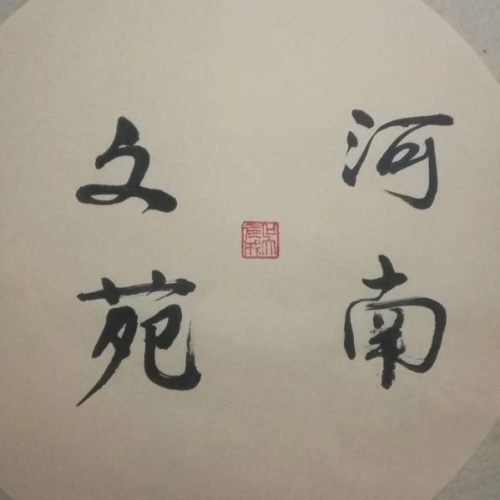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文留随想》(39)我和我终极的情人|匡文留专栏(121)

我和我终极的情人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那就是“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同样也能够“造”出失意者、背运人、倒霉蛋,我和我的同代人,也就是现在扛着个既响亮又不堪回首的“通俗大名”--“老三届”的这些人,其中间就不乏如此者。当然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上山下乡”,一夜之间便把“十年寒窗”一溜烟品学兼优、成绩拔尖、志向宏伟、扬帆远航的我变成了一个漂泊无定的游子,先是在僻远苍凉的山村陷入初恋的纠葛,接着身不由己回城整日价无所事事、无可奈何。十九、二十的黄金季节,假如……不是……我怎么说也正在一流的大学踌躇满志着呢,可……那时,最要命的,就是这样的痛定思痛,这痛,可真是痛入骨髓痛彻心肺啊!
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份工作,管它是啥工作呢,对我来说都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1970年的最后一个月,我成了我们这座城市近郊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集体单位里的一名职工,职业:出纳员;工资:十九元。我把曾经爱不释手的数理化外语语文以及自学过的微机分什么的课本一股脑压进箱底,把插队时和“逍遥”时胡涂乱抹的诗呀文的塞进抽屉,以“凤凰落架”的心境与低调,开始和十来个半文盲式的“社会底层”平民为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尽管大起大落的社会动乱业已平息,举国震惊的温都尔汗坠机事件也已演出,可对于我和我的同代人来说,除了能重新挤入一册城市户籍簿、从而谋到一个无法讨价还价的差事外,依然是看不到任何可以欢欣鼓舞的前景。当时妙龄的我唯一的爱好几乎就是爱穿些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无非就是鲜亮点儿、花样点儿,因而竟闹得满城风雨,满街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见我便尾随身后乱叫“洋气太太”,单位上面的有些“主管人士”竟视我为“异端”。于是,尽管我工作出色,干啥像啥,又尽可能地积极要求进步,却入团入不上,上大学没人推荐,甚至原本定了演样板戏里的铁梅最后都让换了别人,更甚至出差到了上海竟还叫加急电报招了回来。如此种种,二十出头的我便已身心疲惫,自觉“出头”无望,辗转彷徨后不知怎么咱们传统国人的传统观念就盘踞了脑海,那便是:趁年轻找个“郎君”吧,也就有“靠”了。

中国人还有句老话,叫作“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一点儿不假。走背运的我在这一点上更是“命运多蹇”,空怀一腔玫瑰色梦幻和爱情憧憬,愣将少年时代看花了眼的小说中的爱情自作多情地搬到生活中来,看男人只看见了英武的眉眼体态,想婚姻只以为是旅行浪漫风花雪月,结果作茧自缚,一步步陷自己于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丧失人格自由与尊严的“夫管严”的家庭局面。就这样挨着,过着,忙忙碌碌平平庸庸的工作,琐琐碎碎打打闹闹的日子,一双幼小的儿女,无奈飘逝的青春,学生时代骄矜优秀的我早已恍若隔世。要不是岁月在那么一个时辰突然阳光灿烂新辟一条地平线,我很可能会在如上的日子中迅速老去,麻木而无奈。
然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冬天与接踵而来的那个七月,我竟都与之失之交臂,原因再简单不过:“夫管严”。这时我感受到的痛,才叫作真正的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痛,简直在词典上找不到语言能够形容!我是眼巴巴看别人兴冲冲迎机遇而上自己画地为牢坐以待毙呵!
我又想起中国人的另一句老话:“置于死地而后生”。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握手告别的当儿,我开始拿起笔在纸上倾泻我多年积淀的思绪和情感,同时在八十年代第一个夏秋之交“排除万难”考进了兰州大学夜大学中文系。
至此,我与时代一起站在了阳光灿烂的崭新的地平线上,我仿佛大梦初醒,一下子从“文革”开始前的那个品学兼优的高一少年变成了平步诗坛的青年诗人、本科生,其间十几年的迷惘、彷徨、晦暗、疼痛、无奈……被尘封进梦的深处。五年夜大的头四年,我仍旧在原来的厂子当工人,每天晚上一下班,赶紧换下油污的工作服,手都顾不上洗净就沿途胡乱买点儿馒头面包的,挤乘、换好几路公共车赶一个多小时的路去课堂上课。下了课早已时至午夜,回家途中有好大一程没了末班车,我便咬牙自给自壮胆步行往家走。夏日里或风或雨,一身汗一身泥还好说,严冬可就惨了,冰天雪地,耳朵鼻头冻得没了知觉,内衣却粘湿在脊梁上。可原来爱学习的那个灵魂一旦苏醒便没治了,就这样我几年来门门功课都是高分,几乎是最高分,直至毕业。同时我写诗写得入了迷,口袋里总装些小纸片,工余、课间,尤其是公共汽车上和休息日,脑海里就没停了构思,一有灵感,马上落笔。1984年夏天,我生命中实质性的转折终于到来,我以在全国报刊发表诗作几百首、已颇有影响的青年诗人的名义和优异的成绩考入省广播电台任文学编辑,翌年,命运叫我乘上了“独身女人”这只“诺亚方舟”。当生活叫我只能选择坚强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坚守了这唯一的选择。我明白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起码道理,我知道哪怕即使今后的路会走得再崎岖坎坷,我终极的情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诗。

我在最近出版的被誉为“当代论语”的《中国作家3000言》一书中写道:“为诗的人生,人生如诗。”我又在另一句“人生观”中说:“我愿每天即是春天又是秋天,播种和收获永远共存。”我耕耘电台的本职工作可谓业精于勤,仅已经两度荣获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便能够证明。我对诗歌与文学的情有独钟更是桃李不言,书柜中赫然印有“匡文留著”的十四部诗集、散文集无比真实地讲述着我与这世界的相互倾诉和聆听。当然,我还没有轻忽身为母亲的神圣职责,有我父母的呵护与担待,被我称为“我最得意的作品”的一双儿女而今青春焕发、正展羽翼。我还有什么可懊悔和遗憾的呢?……
长长的历史是长长的画卷,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其实这故事写得好写不好,其根本永远在这么三点,那就是:生命的本能与内质;生活赐于你的机遇;你对待机遇的能动性和信念的坚强。读读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故事,生活中永别说“晚”,那么,你每天都可能面临一条阳光灿烂的崭新地平线。
1998年12月28日

匡文留,当代著名诗人。满族,生于北京,长于大西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记者。现在北京兼职、写作。获“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首届唐刚诗歌奖终身荣誉奖。
1980年步入诗坛,在全国二百多家报刊发表诗作三千多首,作品被收入百余种选集并介绍到国外。出版诗集《爱的河》《女性的沙漠》《第二性迷宫》《西部女性》《情人泊》《女孩日记》《匡文留抒情诗》《爱狱》《灵魂在舞蹈》《另一种围城》《古都·诗魂》《我乘风归来》《回眸青春》《匡文留诗选》《大地之脐》,长诗《满族辞典》,散文诗集《走过寂寞》《少女四季》,散文集《姐妹散文》《诗人笔记》《围城内外》,诗论集《匡文留与诗》《匡文留诗世界》,长篇小说《花季不是梦》《体验》《我的爱在飞》,长篇纪实《少女隐情》《我爱北京》《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十部专集。多次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简介与创作收入国内外近百部权威性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