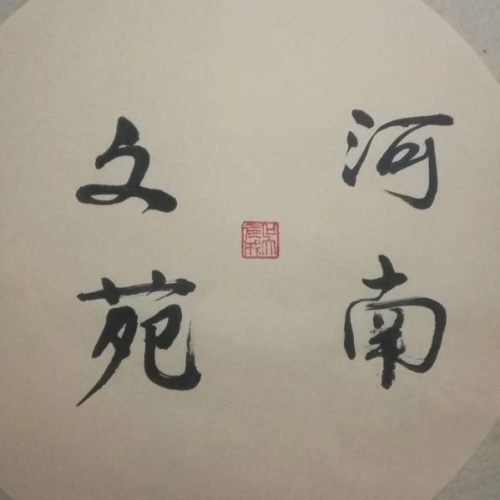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文留随想》(37)母亲眼中的梅娘|匡文留专栏(119)

母亲眼中的梅娘

梅娘这个名字,落寞,孤傲,似有若无地氤氲着某种淡淡的幽怨与感伤气息,不由得便令人脑际闪出“驿外断桥”这样的意境;又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梅妃,一千多年前宫廷之中环宠梅泣的那段故事,总叫这两个汉字像瘦寂一枝斑竹斜斜地割裂了惨白月影,散乱月华珠泪般于无声处了。
不管上述想象与联想准也不准,总之梅娘这个名字很有些传统中国女人味。我这里说的这一个梅娘,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阶段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前期颇有些响动的女作家梅娘。
其实,自小读书看小说也好,还是后来在课堂上学“现代文学史”,梅娘这个名字及标有这个名字的小说对于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并不熟悉,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更是极少有涉。几年前,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著名的女性文学研究家阎纯德先生主编了一套洋洋几百万字、煌煌十卷本的《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因其中收有我的几首代表性诗作和我的妹妹匡文立的短篇小说,我们便各收到了一大套精美样书。当下翻阅,爱不释手,我便从《红杜鹃--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华夏女作家群》这一卷本中发现并记住了梅娘这个名字。一是因为我知道了梅娘是位东北籍女作家,且就生长于吉林省的长春市。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东北人,母亲的老家正是吉林,这大约是一种无意识地源于血脉故园的关注;二呢,则是我看了书中所选的梅娘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侏儒》,深为其干净凝练的笔触、生动细腻的情节和敏感准确的艺术把握而折服。一个私生子、没娘娃备受亲爹“正妻”欺辱的故事。故事不新鲜,过程也简单,却把“我”这个青年知识女性同“傻子侏儒”的几次交道写活了,令人心悸并动情,作品的思想性不露斧痕地得到了升华。
看了便随意说给母亲听,接着将书也拿给了母亲。母亲在吉林市、长春市先读书后教书的青年时代也曾常在报刊上发表些小说散文的,用过的笔名有“杨隐君”“林潜”之类,也应属作家之列。“梅娘?不就是孙德芳吗,那是我同学呀!”母亲眼中掠过一丝光亮,富有表情地说。接着边读作品边慨叹几句,“后来很少见她的名字更不知道情况,谁知现在怎么样了?……”

过了一段我无意中翻有一期的《知音》杂志,看到了采访梅娘及梅娘自己写的目前生活状况的文章,还附有一张近照。一位很平凡的老太太了!照片中的梅娘蓬一头随意的华发,沧桑里透着朴拙和一丝硬朗,简衣素服,典型一个平民化十足的东北老太太。这和“梅娘”这两个方块汉字从表面到内涵所散发着的那些诗情画意简直相距太远了。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不是若有所思地掠过一丝苦笑,更搞不清这苦笑究竟是缘何。只记得回家顺便告诉了母亲一句:《知音》上有梅娘近况,后半生似挺艰辛坎坷,现在特平凡一个孤老太太。活得还挺硬朗。还有言下之意,那便是:真看不出这样一个东北老太太当年竟写得出那么好的小说!拥有了那么一个孤傲、冷艳的芳名!
有评论文章将张爱玲与梅娘并提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上的“南张北梅”,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客死彼岸异域的孤老太张爱玲同曾经红极一时上海滩的那位世家才女、美艳少妇张爱玲又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呢!……岁月啊,万劫不复的岁月……我蓦然愣怔得如坠深渊。
近时,病中的母亲易怀旧,跟我聊着她远留于松花江畔的青春时就聊到了她那时的同学梅娘。《知音》杂志中黑白照片上那个极普通的孤老太太,便秀丽可爱地笑声溅起松江的浪花走到了我的眼前,接着又走进了我的稿纸。
三十年代中叶,少女时代明艳照人的母亲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附设高中部念书。大约是高一下半年的时候,班里插班转来一个女孩子,高个,很结实的模样,蜜色的健康皮肤,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很引人注目,显得聪明又有内涵。女孩子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穿着既朴素又大方,待人亲切热情。一向自恃才高且不流俗的母亲与这位新同学一见如故,很快相处默契。这女孩子名叫孙德芳。
当时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吉林市,是吉林省的首府所在,文化名城,风光旖旎,少年金日成就在市里的毓文中学读书。松花江宛若一条缎带系于吉林市腰际,新修的第一座江桥凌空而越,把两岸的名胜景点龙潭山、小白山、圣母洞等串接起来,松花江冬滑夏泳的欢乐就流过了少女们浪漫的岁月。
出自半知识半官宦之家的孙德芳自幼丧母,和继母的相处自不会愉快,这个大小姐却与家中老保姆相偎亲近,呼之为“大娘”,很引得不少同学不屑。然孙德芳聪明又好强,门门功课都学得棒,深得老师的喜爱。尤其是英文、日文、国文,回回考试名列前茅,连原本“拔尖”的母亲都不能不刮目。班上的国文老师何霭仁,很有些风流才子模样,虽系师范毕业,对新文学却多有造诣,他格外赏识孙德芳,每周一次的作文全评了孙德芳高分并作为范文在班里展阅。高三时,何先生将孙德芳的作文结成集,推荐给他一位开私家书店的朋友出版,并亲自题写了书名:《小姐集》。这便是女作家梅娘的处女集。不知今日梅娘还忆念起这位何霭仁先生否?忆念起则又作何感受?
高中毕业后母亲东渡日本留学,起始进了东京东亚补习学校学日文,孙德芳则到长春一家报社工作。何霭仁已先母亲一步作为教师留学生来东京高师进修,此时对人地两生的母亲挺照顾,联络学校,介绍房东,熟悉环境,云云。母亲便常见何先生兴冲冲捧读孙德芳的来信,每信首必称“亲爱的先生”。母亲笑道,先生您多高兴啊。德芳文章好字也漂亮,真是高足呵。何先生往往莞尔,不无情深道:“她一向如此。”

后来母亲度假回国,在长春见到了孙德芳,聊起女孩儿家的小“隐私”,她嗔曰:我喜欢的那人没见到,不喜欢的那个又来了。讨厌!原来孙德芳一入报社,便引来了两位热烈的追求者,她“喜欢的那人”,正是不久便成了她的丈夫的柳龙光。柳龙光那时已在报界小有名气,一支笔洒脱干练颇受重用。孙德芳真好福气!这便是母亲和孙德芳最后一次晤面,此后天各一方,落红如雨,飘逝的华年早阒寂无痕。
再后来母亲回国到长春市第一女子中学执教,听说孙德芳同夫君一起去了华北《武德报》任职,柳龙光即报社社长。据说该报表面系日本人投资所办,实际上是担任抗战工作的。于此不再多言。也就是这前后,有读者在长春某报上看到孙德芳翻译的日本长篇小说《白兰之歌》开始连载,始署名“梅娘”。
登上文坛的梅娘生活却走开了下坡。先是柳龙光患不治之症英年早逝,接着三个孩子夭折了两个,精神遍布疮痍的梅娘只身带孩子回返东北老家四平。
转瞬半个多世纪倥偬而逝,一头华发满脸沧桑的平凡东北孤老太太梅娘,你在杂志的黑白照片上注目人世,谁解得了其中滋味?
母亲给我讲到这里,依旧生动的一双大黑眼睛透过满颊深而密的岁月辙痕掠过沉沉的感伤,轻叹道,假如我们现在相见,定会紧紧拥抱的……
我无语。这个“假如”大约是个永远名副其实的“假如”罢了。
1998年12月20日

匡文留,当代著名诗人。满族,生于北京,长于大西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记者。现在北京兼职、写作。获“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首届唐刚诗歌奖终身荣誉奖。
1980年步入诗坛,在全国二百多家报刊发表诗作三千多首,作品被收入百余种选集并介绍到国外。出版诗集《爱的河》《女性的沙漠》《第二性迷宫》《西部女性》《情人泊》《女孩日记》《匡文留抒情诗》《爱狱》《灵魂在舞蹈》《另一种围城》《古都·诗魂》《我乘风归来》《回眸青春》《匡文留诗选》《大地之脐》,长诗《满族辞典》,散文诗集《走过寂寞》《少女四季》,散文集《姐妹散文》《诗人笔记》《围城内外》,诗论集《匡文留与诗》《匡文留诗世界》,长篇小说《花季不是梦》《体验》《我的爱在飞》,长篇纪实《少女隐情》《我爱北京》《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共产党》等三十部专集。多次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简介与创作收入国内外近百部权威性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