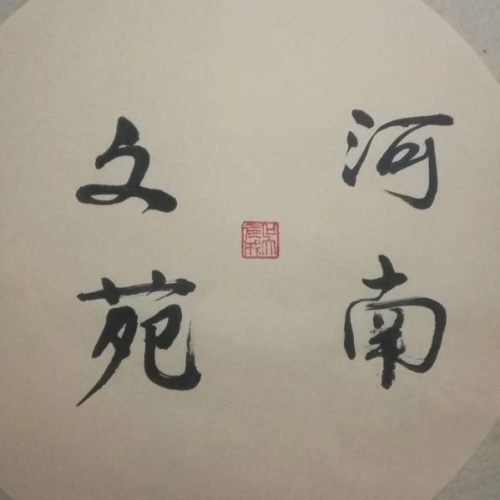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柴扉集》(16)不散的年味儿|张国领专栏(104)


现在每当过年的时候,总会听到有人抱怨这年过得越来越没年味儿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年味儿呢?这很难有个标准,每个人心中的年味儿应该是不同的,不是年味儿不同, 是所在的地域不同、历经的年代不同、身处的社会背景不同、生长的家庭环境不同所决定的。
我小时候就特别盼过年,现在想来盼的是什么呢?是穿新衣、放鞭炮、吃美食、得压岁钱,跟着大人到处去拜年。还有初一初二这两天是不用帮大人劳动的,可以放心大胆玩两天。
现在的美好生活下,这些儿时盼望的东西,都成了日常必备。鸡鸭鱼肉天天有,鞭炮禁放,新衣可着劲穿,零花钱没断过,微信短信手机随时可以联系沟通,还盼望什么呢?对年的期盼少了,自然觉得年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其实人在意什么,正是那件事里有他的期盼,有了期盼的事情就有无限的吸引力,一旦期盼没了,或淡了,说明事情本身的魅力也就不再了。
现在想来,年味儿是渐渐变淡的。
记得住进“高干别墅”之后,在合肥过的第一个年,是我自己写的对联,初衷是为了省下买对联的钱。
对联是结合我个人的实际写成的,没想到写出了特色,引来不少人围观,这也激发了我写对联的兴趣,后来连续几年的春节,都不再买对联。
鞭炮是过年的标配,所以无论在哪过年都少不了。尽管每年春节之前领导都要要求各单位搞好节日安全教育,尽量少放鞭炮,那年我还是买了一堆各种鞭炮。一般燃放鞭炮都是年三十晚上到大年初五,可我孩提时代的习性没改,将成挂的鞭炮都拆下来弄散了,装在口袋里,时不时地掏出一颗点燃,往空中一扔,“啪”的一声响,一是烘托节日的气氛,二是让别人知道我也是有鞭炮放的人。

年二十八的晚上,吃过晚饭我照例从整挂鞭炮上拆下几颗准备点燃,不料就在拆的过程中,左手拿着的香烟碰到了鞭炮的药捻子上。要拆的没拆掉,没拆的从中间炸开了花。接着就是噼呖啪啦火光四溅,烟雾很快在整个房间弥漫,浓浓的火药味向四周迅速扩散开来,将我笼罩在烟雾中。这时候接水灭火是来不及了,吓得我提起身边的暖水瓶就往活蹦乱跳的鞭炮上浇。响声很快被压制下去,不过不是我浇水的原因,是一挂鞭炮炸完了。
好一会我才回过神儿来,等我回过神儿来才明白,浓浓的年味儿里原来还隐藏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啊。
“高干别墅”是五六十年代盖的瓦房,由于我的童心、失误和大意,差一点酿成重大火灾,一身冷汗过了很久才退去。
这件事在离开合肥之前始终是我要保守的最高机密,否则同住“高干别墅”的单身女人、领导司机和秘书都会找领导告上一状,那我挨一顿批评或做一次检讨是跑不掉的,因为这件事直接威胁到了别人的人身安全。
合肥过年的习俗与我老家河南过年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老家大年初一全家团聚,从初二开始走亲戚拜年,合肥却是从大年初一就开始相互拜年了;我老家拜年带的礼物都是果子和甘蔗,合肥无论去谁家都带大蛋糕,初一到初五,大街上都是提着蛋糕到处走的人。有的除蛋糕之外还带两瓶酒或烘糕切糕之类的。
蛋糕被你家拿来又被我家送去,却很少有人吃,当时合肥人很形象地把这种拜年称作蛋糕大游行。有细心人还做过一个试验,在自家买的蛋糕上做了一个记号,初一送出去之后,不到初五,这个蛋糕就又回到了他的家中。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很少有私家车,出门都骑自行车,礼物被夹在后座上,可蛋糕和酒瓶都是圆的,自行车上不好固定,所以你时常能看到骑车人走着走着蛋糕就从车上掉下来的尴尬场面。
现在的饭店过年也照常营业,家里来了客人大都去饭店吃饭,既省事又省钱,花钱买的是档次和清静。那时还没有去饭店请客吃饭的习惯,这一部分原因是饭店吃饭少了家的味道和气氛,另一部分原因是刚刚走进温饱的时代,钱还是紧张,所以来了客人都在家中烧饭。
我在合肥没有亲戚,除地方有几个朋友,就是部队比较要好的战友。战友之间过节不需要地方那种提着蛋糕大串联的俗气。
我们节前就商量好,春节期间从谁开始轮流坐庄,就是一家一家轮流相聚,顺序排好了时间上就不会冲突,万一谁那天有事不能到场,其他人照常进行。

不过不拿蛋糕也不会空着手去吃饭,毕竟是过年,拿什么?我们是喝酒人,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去谁家,自行车筐里都带四瓶酒。
当时比较流行的酒都是安徽产的,什么高炉大曲、明光大曲、醉三秋。好一点的有口子窖、古进贡酒等。放假几天几乎天天相聚,无论到谁家都是热热闹闹喝一场,海阔天空吹一通,你长我短论一遍,说多了说少了没人在意,说错了说对了没人计较,天天都异常尽兴。完了事不管喝多喝少,醉与不醉,骑上自行车就回家,当然从自行车上摔下的事也时常发生。
过节前估计有多少人来家里吃饭大致心中是有数的,采购年货时,需要买什么、买多少,能做到八九不离十,为了防止有意外的人员到来,一般都会多备一些。
可轮到我做东那天,却出现了意外。地方两个朋友知道我是第一年在合肥安家,他们分别带着他们的朋友到我家拜年,两天两拨人,把家中的大部分食材都耗去了。
第三天战友们相聚的时候,凑一桌丰盛的饭菜已是捉襟见肘。街上卖东西的回家过年了,商店还没有开业。家中现存最多的副食只有排骨,我和妻子就商议把排骨全煮了,装进一个大盆里,我家餐桌是借别人的,桌子不大,盆子往桌中间一摆,周围就只够摆下几个小碟子,虽然菜的品种看起来不多,排骨也算是好东西,管吃饱没问题。到时我还可以用河南老家的方式敬酒,酒喝多了谁还会在意菜的好坏呢。
为了多上一道菜,妻子积极想点子,最后想到了把排骨肉剔下一部分剁成馅儿,装进掏空了的苹果里,放在蒸笼上蒸。
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发明,估计菜谱里找不到这道菜。蒸上之后我对这道菜充满了期待,因为在别人家中都没吃到过,一定会让客人有新鲜感。哪知结果不但没有出彩,这道菜还变成了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
蒸熟之后的红苹果变成了褐黑色的烂苹果,关键是苹果里面的馅儿出奇地难吃,谁尝谁皱眉头。创新发明一下子变成了砸牌子工程,看来这是随意尝试不在谱的东西,让我付出的惨痛代价。
不过那天的一盆排骨基本消灭干净,大家都很满意,临走时都一再表示感谢。
过了两天我去地方一朋友家拜年,他是个官二代,家境优渥。中午吃饭时,他妈妈除了炒菜还专门炖了排骨汤,吃饭时先给我盛了一碗排骨。我接过碗才发现,一碗清清的汤水里,只有一节两寸长的排骨,外加两片青菜叶儿。汤的味道倒是非常鲜美,可那毕竟是汤水啊。看着那一节排骨我实在不忍心把它吃下去,因为它显得是那么精致、贵重、豪华、玉骨临水、卓而不群……
端着那碗排骨,我突然想起我炖的那一盆排骨来,如果熬成这样的汤,不知能熬出多少碗呢。可我要也这样炖排骨了,那我还是河南人吗?
年,每年都过。那种提着蛋糕走亲戚的过年,骑着自行车带着酒挨家轮流吃喝的过年,自离开合肥之后就没再经历过。
工作调动到北京之后,隔壁邻居、对门邻居都不相互串门,好像人与人之间都要时刻提防着什么,首都的人情原来是如此冷漠。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年味儿丢失的时候,我觉得丢失的不是年味儿,而是人间最珍贵的人情味儿。
人情味儿丢失了,无论活得多么风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与人之间如果只剩下利害关系,转身之间也就没什么值得回想、念颂的了。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