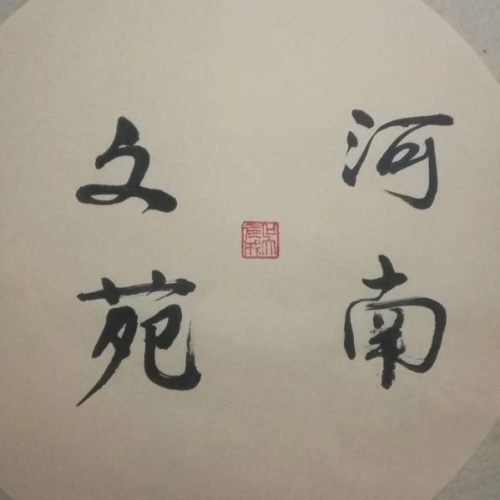在C与O之间(节选)[短篇小说]||马晓康专栏(一)

马晓康
原载:人民文学 2024年05期

这世上有许多叫小勇的人,但从小留辫子的小勇估计只有一个。他是我的小学同桌。
镇子上的人都知道,小勇的奶奶逢人便说小勇是观音菩萨身边的童子下凡,将来要干一番不得了的事业,那根又细又长的辫子就是菩萨托梦让留的。我看过电视,见过菩萨身边的童子,他们可都是白白净净的小孩。再看看小勇,长得又黑又瘦又小,像只猴子。老师教育我们不要理会封建迷信,所以我经常揪那根辫子玩。说是揪,其实只是好奇,拿起来端详端详,不用力的。我刚捏住那根小辫儿,小勇就喊疼,好像我真使劲拽了似的。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嘟囔一句,胆子真小,还小勇呢。
我学习比小勇好。考试的时候,小勇总想偷看我的试卷。我怎么可能让小勇得逞?我每写完一道题,就用左手捂住,等捂不过来的时候,就用垫板盖住。小勇在旁边急得龇牙咧嘴,嘴里发出各种奇怪的暗号,有时还会偷偷碰碰我的手肘。我没有向老师告发他,反而抿着嘴偷笑,他着急的样子让我感到享受。
你把我拽笨了。每次出成绩,小勇都会拿着那张满是红叉叉的卷子找寻我。
我不确定小勇是不是真的被我拽笨了。在我的认知里,把人拽笨可能是犯罪。我不想犯罪,只好攥起拳头回一句,你本来就笨。说完,我还不忘再捏一下他的辫子。这时小勇就叫得更惨了,好像被踩住尾巴的猫。
为了这事,他没少跟老师打我报告,老师也没少教训我。可我还是忍不住去揪。老师问我,为什么只欺负他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欺负小勇,只是觉得这辫子好玩。老师又问我,为什么只揪他一个人的?我说,老师,班里其他同学也没有这样的小辫儿呀,我总不能去薅女生的辫子吧,那是流氓才做的事。
老师气得把我拎了起来。我不服气,继续狡辩,不止我一个人揪过他的辫子,坐在我们后面的女生李小花也揪过,他就从来不喊疼,还告诉她随便欣赏不收门票。
到教室外面罚站去!老师厉声说。
站在门外我颇为得意,我是全班唯一不用听课的人。光秃秃的院子里,除了门卫老头打过一趟水,一位老师骑车买回来三张烧饼,再无他事。我试着数院子里的坑,今年植树节的时候我们曾在这些坑里种树,后来又挖走了。大概数到三个教室那么远,我就看不清了,挖坑的土堆挡着其他土堆,不确定后面还有两个还是三个坑。隔壁班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读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突然感到某种让人想哭的孤独。好在那会儿是秋天,风送了许多落叶到我脚下,有梧桐树的,也有杨树的。它们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趁老师不注意,弯腰去捡。它们粗细不一,我像在挑选趁手的武器将它们捏来捏去,很快便薅出一大把乌黑的富有韧性的叶把儿,它们散发出清香的味道,攥在一起,像电视上的集束手榴弹。
下课后,我坐到课桌上向小伙伴们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小勇眼馋,伸手就跟我要。
马哥马哥,给我几根吧。我去帮你打败隔壁班的人。小勇摇晃着我的腿。
你刚才还告老师害我罚站呢,不给。
给我吧。以后我的辫子让你随便抓,只要你别使劲拽就行。
不需要。别等期中考不好了又说我拽坏你的脑子。我晃了晃手中的“集束手榴弹”,撇过头对围观的同学们说,看到没有,这种乌黑又拉不断的,最有劲儿了。昨天小勇拿了一堆梧桐树叶子的,根本不行,中看不中用,根本抗不过别人,一抗就断了,太脆生了,给我们班丢人。你看看咱这个,怎么弯都没事,抗手指头都拉得手指头疼。说着,我把“集束手榴弹”放在屁股边上,挑了一根中意的套在手指上拉了起来,手指被勒出深深的红印。
你给我一根吧,就你手上的这根。等我赢了回来请你喝冻冻蛋(一毛钱一袋的,冻成坨的汽水)。
给你也行。你得给我表演个节目,学点儿啥。
你说,学啥?
学个猴子吧。都说你长得像猴子。
不学。
那就学你奶奶。老猴子。说到这里,我捂嘴大笑。不等小勇表演,我先抓起旁边一位男同学的手,学着小勇奶奶的样子,眯缝着眼睛缩着嘴唇,用一副天塌了的语气说,不得了咧,俺家勇勇是观世音菩萨身边的童子下界。我梦见咧。天上那颗星星就掉俺在屋里咧。不得了咧。
小勇使劲推了我一把,我比小勇壮实很多,没推动。小勇转身要跑。我伸手抓住他的小辫子,向后一拉。
吧嗒。我觉得手心一凉,手里躺着几缕垂头丧气的头发。再看小勇的后脑勺,本就不粗的辫子,只剩几根毛在空气中手舞足蹈。

我妈是当着小勇爸妈的面打我的。我爸妈和小勇爸妈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打我说不过去。我怀疑我妈小时候被我姥姥打多了,打我的时候特别用力,我疼得嗷嗷叫,就像姥姥家被剪了尾巴的小猪。他妈拉着我妈说,算了算了,孩子这辫子六周岁的时候就该剪了。这是他奶奶非让他留的。你也知道,他奶奶原来是干神妈妈的,说菩萨托梦让留到十二岁。我们都说不能留那么长时间的,断了也好,断了也好。不搞迷信。
这一劝,我妈打得更来劲了。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脸已经肿得像猴屁股了,轻轻一碰便胀痛得不行,仿佛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要不是小勇出来说了一句,阿姨算了,别打他了,我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
升到三年级,所有学生都重新调班,小勇居然还是我的同桌。我们换了新班主任。她是一位烫头的妇女,教英语。在她手下上过课的五年级同学说,她最喜欢用小木板打手心,比巴掌扇在脸上还疼。做错一道题挨三下,不及格的要打二十下,全班同学一起数。在她教学的日子里,常有同学被打得痛哭流涕,我们一面嘻嘻哈哈笑,一面又怕下一个被打的是自己。高年级的前辈们嘱咐我,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把字写大一点儿,这老师眼睛不好,有些同学因为字写得太小被认错而挨打。
我是好学生,字也写得够大,所以我不用担心挨揍。谁让我英语好呢,一直是班里第一,班主任也舍不得打我,偶尔错了一些不该错的题,班主任也只是象征性地在我的手心点几下。我妈对我说过,我们班主任的丈夫老魏和我爸关系好,是酒友。为了把班主任调到我们镇,我爸还帮忙找了人。她要是揍我,那就是恩将仇报。老魏和小勇爸妈的关系倒是不好,老魏和小勇他爸都教数学,觊觎小组长的位置。小勇他妈经常去打老魏的小报告,光是校长那儿收到的匿名信就有六封,说老魏生活作风有问题。
信以为真的班主任号啕大哭着冲到老魏办公室,结果把和老魏长得极像的副校长抓了一脸花。这场闹剧不光我爸妈单位的老师们知道,就连我们小学的一年级小孩儿也能说得有声有色。我不知道这次风波是如何平息的,大概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大家就不怎么提这件事了。
这次考试,咱们班考得相当刺毛(差)。除了马大胖同学捣鼓了个九十分,不及格的占了一多半。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几位班干部正在帮着课代表发卷子。
平时和你们讲的知识点怎么都不往脑子里去呢?特别是第三题,考试前才讲过这些单词。来,做错这题的都给我站起来。说着,班主任抄起小木板,在讲台重重地拍了一下,仿佛是阎罗殿的判官砸下了惊堂木。同学们吓得直打哆嗦,就连明知不会挨揍的我都免不了心头一颤。讲台上粉尘四溅,呛得班主任直咳嗽。今天小勇是值日生,我都跟他说多少遍了,直接用拖把沾水擦,一下就擦干净了,用擦子除了搞得一屋子粉笔末,没点屁用。用拖把还有个好处,那就是老师来早了也写不成字,没法占我们课间。
来。做错的给我站起来!尘埃落定,班主任平复嗓子后喊道。
包括小勇在内的三十多名同学站了起来。
班主任走到第一位同学面前,问道,来,你给我说说,这些单词你是怎么记的?“red”中间不是填e吗,你怎么给我填了个a呢?这是个什么词?来,伸出手来!
不等这位同学说话,老师直接抓过他的左手,他乖巧地伸直了手掌。我和他隔着四排同学,我聪明的大脑计算着,他的手或许还不如班主任的手一半大。
啪!
啪!
啪!
这位同学是好样的,流着眼泪,却没有哭出声。他要是进了电视剧,肯定不会当汉奸。
来,看看下一道题,这个“blue”你是怎么填的?应该填u的地方你给我捣鼓成了c,你告诉我,“blce”这个词是哪个老师教你的?来,伸手!
今天班主任的心情格外好,她不像以前那样上来就打,而是认真指出每位同学每道小题做错的点,纠正他们的错误,给予他们正确答案,然后才让他们体会到切肤之痛,明白犯了错误要挨打的道理。
整节课啥也没学到,光看班主任打手掌了。直到下课铃声响了才轮到小勇。
按理说,你这次表现得还可以,及格了,但你还是写错了一个单词。为什么把“black”写成了“blaok”?是你妈在家里教你的吗?班主任抓着小勇的手问道。
老师,我没写错,我写的是c。您再看看。小勇急得甩胳膊跺脚,班主任牢牢抓着他的左手。我想起上周六我妈去集上买的母鸡。当时我妈就这样抓着鸡的两只翅膀,任由它在那儿扑扑腾腾。回到家的时候,我妈还从篮子里掏出了一只蛋。
班主任很负责任地拿起小勇的试卷,对小勇说,我看了,你写的就是o,怎么可能是c。
老师,真的是c,不是o。小勇哭了出来。全班同学都笑了。
你看看这是c还是o。班主任转身,把卷子递给后面的李小花。李小花其实是我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头上总是别着一朵大红花,长得还很漂亮。李小花认真地盯着卷子,似乎她就是画在课本里的认真阅览文件的科学家。事实上,她曾大方地对老师和同学们说过,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这次考试她考了八十九分,她是可以被称为我的竞争对手的同学。班主任常用“三天不学习,赶不上李小花”来激励我好好用功。因此,当李小花说出自己的梦想以后,我也用朗诵的腔调说出自己的梦想同样是当科学家。其实我想成为学校门口炸火烧的胖老板娘的儿子,那样就有无穷无尽的炸火烧、豆腐乳、辣条吃了。
报告老师,小勇写的是o!李小花站起来,字正腔圆地大声喊道。她双手紧贴着裤线,昂首挺胸,就像昨天早晨当升旗标兵那样。
来,你说说,是c还是o?班主任又问李小花的同桌。
报告老师,是o。这位同桌连看都没看就站了起来,学着李小花的姿势回答。
你还想说什么,小勇?明明是你写错了还不承认。班主任把卷子放回小勇的桌子上,用小木板的一端反复敲着写错的地方。
刘老师,传达室有人找你!教室外面有人喊。
好的马上来。
报告老师,你还没打小勇呢。李小花好心地提醒道。阳光映照着她红扑扑的脸颊,像个小小的女英雄。
下节课再说吧。先下课。班主任说。

我们像撒欢的兔子一样冲了出去。
我去水龙头那儿喝了点儿水。回来后,小勇哭着对我说,马大胖,我们班你是英语最好的,我只相信你。你告诉我实话,这到底是不是c。我明明在中间留缝了啊。
我低头看看他手中的试卷。的确是c,小勇没说谎,非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这个c写得太小太密,像一只蜷起来的瘦小的西瓜虫。若是头部和尾部再长一点儿,就真成了班主任口中的o了。可是,我笃定,小勇写的就是c,因为头部和尾部没有相交,只留了小于一毫米的缝(我用尺子量了)。
可班主任非得说这是o,我真的留缝了啊。
烫头妇女不讲理。小勇,我看得很清楚,你留缝了。要是让我改卷子,你写的绝对是个c。
好的。谢谢你。以后我就跟你混了。说完,小勇拿出铅笔刀割掉了自己剩下的几根长毛,递到我的面前。
你不是喜欢玩我的辫子吗?送给你了,随便玩。
我没有接。
等会儿老师来了,你能不能帮我说一下?你成绩好,老师肯定相信你。李小花他们靠不住。
行。我帮你。我可不是为了你的辫子。我接过了小勇的辫子,自从上次被薅散了,这几根毛变得越来越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谢谢你!只有你跟我说这是c。你出去的时候我问了好几个同学,他们都说是o。只有你看到了这条缝,我真不明白班主任为什么说这是o。
班主任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下节课你就站起来告诉她,刘桂英,我写的是个c,不是o。她要是想打你,你夺过板子就跑,我掩护你。
好的。
上课铃声响了。每位同学都双手叠在桌子上,挺起腰板,等待老师。教室外同别人说笑的班主任,一进教室便立刻板起了脸。她从讲台上摸到小木板,来到小勇面前。
怎么样,现在看明白了吗?“black”这个单词是黑色的意思,这里应该写c,可你却写了个o。来,伸手吧。
班主任没有抓小勇的手,她在等小勇自己伸出来。
老师,我没写错,我写的就是c。马大胖可以为我作证。课间的时候我问过他了。
是吗,你认为这是c吗?班主任用小木板把卷子推到我面前。
没,没有。老师,我没说过。我站了起来,挺胸收腹,姿势比李小花标准多了。真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我这么挺拔的英姿居然不让我当升旗标兵。
人家怎么说没这回事呢?班主任问小勇。
小勇哭着说,课间的时候我问的他,他说你老眼昏花看错了。
报告老师,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大声吼了出来,像电影里向将军作报告的士兵。
来。做错题三下,说谎十下。班主任抓起了小勇的手。
小勇撕心裂肺地哭着,马大胖,你浑蛋,我把辫子都给你了,你答应我说实话的。
报告老师,是他自己割下来塞给我的,我没要他的。不信你可以问班里同学。我目视前方,再次收紧有些松弛的腹部。傍晚的余晖在教室里洒下温柔的金色。望着黑板旁边的流动锦旗,一种神圣的感觉涌上心头。
是他要的,还是他自己给的?班主任转头问后排的同学们。
小勇自己给的。同学们齐声说。
我的嘴角挤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小勇哇哇地哭了起来。
班主任摸摸小勇的脑袋,然后俯下身子,缓缓地将试卷端到面前,翻白眼似的贴上去看。良久,她叹了口气,对小勇说,就当你写的是个c。下次写c的时候,记得让c的嘴巴张大一些。
报告老师,您还没打他呢。李小花举起笔直的右手说道。
算了,你看他哭的这个样儿。女生都比他强。班主任收起了板子。
当天晚上,小勇病了。一开始是发高烧昏迷,醒来后就不会说话了。小勇的奶奶请了几个看事儿的同行,又是念经又是做法,还烧了小人儿。小勇盘着腿坐在床上,看着他们傻笑。小勇的奶奶对着小勇磕头,求菩萨显灵救救小勇。看事儿的人顺水推舟,把问题推到被割断的小辫子上,说那是菩萨让留的辫子,如今辫子没了,就该回到菩萨身边了。这话吓得老太太当场晕厥。小勇家的亲戚来我家大闹,说是我割了小勇的辫子。那天我爸不在家,他们冲进来,砸坏了好多家具。镜子碎片崩在我的脸上,沿着左嘴角到耳郭,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我妈嚎叫着把我护在身后,幸好邻居帮我们报了警。
就在我的血痂最厚、伤口最痒的时候,小勇回来上学了。市里的大夫说小勇得了应激障碍性癔症,坚持吃药就行。班主任给全班同学调了座位,李小花是我的新同桌,我们坐在紧挨讲台的前排,小勇则被换到了后排不起眼的角落。我不喜欢李小花。她刚坐下就在桌子上画了边界线,谁越界了就用铅笔扎谁。小勇从来不这样。我怀念和小勇坐同桌的日子。上课时,我偷偷转头看他,发现他也在看我。
下课后,我走到小勇面前。一周多不见,小勇变胖了,变得陌生了。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小勇那只有几根毛的辫子。
我们还是好朋友吗?我问。
小勇接过纸包,对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5期)

马晓康
一九九二年生,祖籍山东东平,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在读博士。写小说、诗歌,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文、韩文等。曾获泰山文艺奖、《诗选刊》年度优秀诗人奖、中国长诗奖、韩国雪原文学奖海外特别奖等。